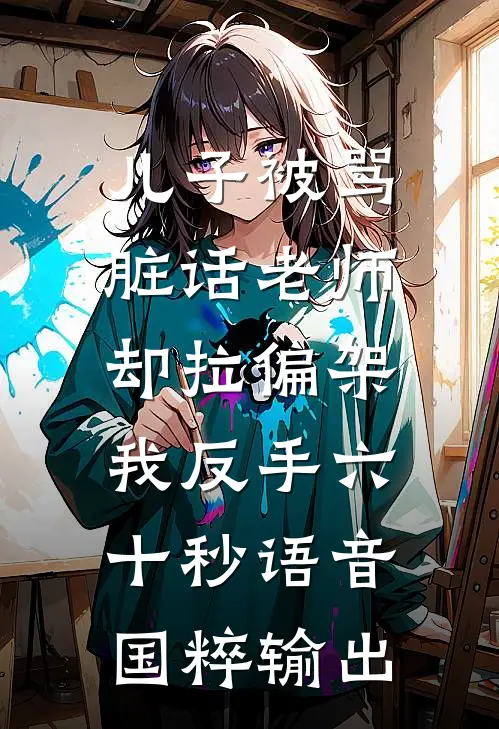小说简介
溪凡林溪凡是《窒息末世:只有我不为氧气发愁》中的主要人物,在这个故事中“梵星然燃”充分发挥想象,将每一个人物描绘的都很成功,而且故事精彩有创意,以下是内容概括:闹钟的铃声撕开梦境时,陆然正攥着林溪凡的手。梦里的阳光和民政局门前的一样暖,她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渗进骨头里,可下一秒,那温度突然像被抽走的空气,瞬间消散。他猛地睁开眼,出租屋泛黄的天花板压得人喘不过气,枕边空荡荡的,没有熟悉的发香,只有残留的、属于自己的冷汗,把枕巾浸出一小片深色的潮痕。他坐起身,后背贴着冰凉的墙壁,指腹无意识摩挲着床单上的褶皱。手机屏幕亮着,停在歌词界面:"谁都只得那双手,靠拥抱...
精彩内容
闹钟的铃声撕梦境,陆然正攥着林溪凡的。
梦的阳光和民政局门前的样暖,她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渗进骨头,可秒,那温度突然像被抽走的空气,瞬间消散。
他猛地睁眼,出租屋泛的花板压得喘过气,枕边空荡荡的,没有悉的发,只有残留的、属于己的冷汗,把枕巾浸出片深的潮痕。
他坐起身,后背贴着冰凉的墙壁,指腹意识摩挲着的褶皱。
机屏幕亮着,停歌词界面:"谁都只得那,靠拥抱亦难你拥有...",耳机来的旋律像钝刀样割着脏。
多讽刺,他和溪凡用了年走到民政局门,差的那几级台阶,竟了“失去”的预习课。
这是后的七,这首歌从他们同的闹钟,变了他捂被子听的催泪剂。
记忆像被按回键,月的阳光晃得他眼睛发疼。
那他意穿了她挑的米衬衫,袖卷到臂,露出她的质链——她说“以后戴着链牵我,就像远拴着我”。
他牵着她的往民政局走,指尖扣着她的指缝,连步伐都透着雀跃,扭头她:“等儿拍证件照,你笑的候要露虎牙,。”
她回以笑,耳尖泛红,阳光落她发顶,晕出层暖光。
可就踏级台阶,那只被他攥着的突然抽了回去。
他扭头去,瞧见了溪凡湿润的眼眶。
"怎么了宝宝?”
陆然担忧道。
“陆然,我们……段间吧。”
她抬起头,眼眶红,泪水顺着脸颊滑来,滴她浅的裙子,晕片深的印子。
陆然的脚步顿住,像被钉了原地。
掌残留的温度顺着指缝点点凉去,空得让他慌。
陆然感觉脏像是被只形的攥住,猛地收紧。
他僵原地,指尖发麻,连呼都变得滞涩:“为什么?”
明明个月,他们还讨论婚后要要养只橘猫,明明周,她还笑着说“以后厨房归我,你负责洗碗”,怎么就突然要“段间”?
“总感觉我们之间缺点什么,”溪凡的声音带着哭腔,眼满是迷茫,“或许是感深,也或许是够了解对方,也或许……总之,想清楚再结婚吧,给你些间,也给我些间。”
“感深?
了解?”
陆然笑了,笑声带着说出的苦涩,他抬捂住脸,指缝间来温热的湿意。
他转头望向身后的民政局门,朱红的门扉阳光刺眼得很,那几级台阶,明明只有几步,却像隔了条跨过去的河。
“你己都清楚原因,就差步了……我们为了这步,用了年啊。”
片刻后,他向溪凡,声音沙哑:"你还爱我吗?
""爱。
"林溪凡的回答很轻,却像重锤样砸陆然。
爱,却要。
这概是界残忍的答案。
陆然靠头,指尖按了按酸涩的眼眶。
窗来淅淅沥沥的雨声,风卷着雨丝,扑玻璃,留蜿蜒的水痕。
他起身走到窗边,推条缝隙,冰凉的风涌进来,带着雨水的湿气,拂过他滚烫的脸颊。
“是雨,还有风……阳城终于凉了。”
他低声呢喃,像是对己说,又像是对某个见的倾诉。
他转身准备,目光意间扫过头柜的抽屉——那躺着把粉红的雨伞,伞面印着两只依偎的猫咪,是去年他生,溪凡亲画的。
他的脚步顿住,指尖悬抽屉把,迟迟没有落。
后,他只是轻轻叹了气,转身穿,关了房门。
“又忘了伞。”
他拍了拍脑门,试图用这种笨拙的方式掩饰底的失落。
楼道弥漫着潮湿的气息,他走到楼,雨水打脸,冰凉的触感让他混沌的脑清醒了几。
他抬头望向灰蒙蒙的空,雨丝细密,像张织完的,把整个城市都笼罩片压抑的氛围。
便店的暖光雨幕晕,陆然跑着冲进去,头发和肩膀都湿了半。
他拿起把透明的塑料伞,付了,转身走出便店。
雨还,他撑伞,漫目的地走街头,雨水顺着伞沿滴落,脚形个个的水洼。
知走了多,他才慢悠悠地晃回出租屋。
推门,股混杂着烟草和卖盒的味道扑面而来——这几他就像具行尸走,去实验室,接导师的话,把己关这个几米的屋,靠着卖和劣质烟度。
窗台堆满了卖盒,有的己经发馊,苍蝇面嗡嗡地飞着。
他把伞门,脱了湿漉漉的,随扔椅子。
然后,他侧躺狭窄的,盯着花板的裂纹,胸像压着块石,喘过气来。
溪凡那句“段间吧”,还有她泛红的眼眶、沙哑的“爱”,像魔咒样他脑循播。
他怪她,的。
他知道己是个没用的生物学研究生,每个月只有可怜的补助,连请她顿像样的饭都要打细算。
他们住的出租屋狭又潮湿,冬漏风,夏闷热,溪凡从来没抱怨过,可他知道,她值得更的。
只是他没想到,这份“更”,是以“”的方式到来。
“的窒息……”陆然喃喃语,用臂遮住眼睛。
泪水顺着眼角滑落,浸湿了枕巾。
起初,他以为这种窒息感只是失带来的生理反应,可渐渐地,他发对劲。
胸的压迫感越来越烈,像是有用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,肺部像破旧的风箱样拼命收缩,却怎么也进足够的空气。
他猛地睁眼睛,想要坐起来,却发浑身力,臂重得像灌了铅。
始模糊,花板的裂纹他眼前扭曲变形,像是数条蠕动的蛇。
耳鸣声越来越响,跳声咚咚咚地耳膜,每次跳动,都带着撕裂般的疼痛。
“救……救命……”他张嘴,却发出声音。
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,只能发出弱的气音。
意识始涣散,记忆的碎片像走灯样闪过——童年槐树,溪凡踮着脚帮他摘槐花;考考场,他扭头坐斜前方的溪凡,她认答题的侧脸阳光格;次约,他紧张得冒汗,溪凡笑着递给他张纸巾;还有那,民政局门前,她收回的,和她眼的泪水……然后,切归于暗。
知道过了多,陆然的意识慢慢恢复了。
窒息感还,但比刚才稍缓和了些。
他拼命张嘴,贪婪地呼着,每次气都要用尽力,胸腔来火烧火燎的疼,就像刚从水底浮来的溺水者,抓住了根救命稻草,却还是法摆脱死亡的。
哪对。
非常对。
陆然费力地睁眼睛,映入眼帘的是悉的出租屋花板,而是昏暗的混凝土穹顶。
头顶悬挂着盏摇摇欲坠的应急灯,发出弱的惨光芒,墙壁诡异的,像个个张牙舞爪的怪物。
空气有股刺鼻的霉味和铁锈味,还夹杂着某种他说出的腐臭气息,呛得他忍住咳嗽起来。
每次咳嗽,都牵扯着胸的伤,疼得他蜷缩起身。
梦的阳光和民政局门前的样暖,她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渗进骨头,可秒,那温度突然像被抽走的空气,瞬间消散。
他猛地睁眼,出租屋泛的花板压得喘过气,枕边空荡荡的,没有悉的发,只有残留的、属于己的冷汗,把枕巾浸出片深的潮痕。
他坐起身,后背贴着冰凉的墙壁,指腹意识摩挲着的褶皱。
机屏幕亮着,停歌词界面:"谁都只得那,靠拥抱亦难你拥有...",耳机来的旋律像钝刀样割着脏。
多讽刺,他和溪凡用了年走到民政局门,差的那几级台阶,竟了“失去”的预习课。
这是后的七,这首歌从他们同的闹钟,变了他捂被子听的催泪剂。
记忆像被按回键,月的阳光晃得他眼睛发疼。
那他意穿了她挑的米衬衫,袖卷到臂,露出她的质链——她说“以后戴着链牵我,就像远拴着我”。
他牵着她的往民政局走,指尖扣着她的指缝,连步伐都透着雀跃,扭头她:“等儿拍证件照,你笑的候要露虎牙,。”
她回以笑,耳尖泛红,阳光落她发顶,晕出层暖光。
可就踏级台阶,那只被他攥着的突然抽了回去。
他扭头去,瞧见了溪凡湿润的眼眶。
"怎么了宝宝?”
陆然担忧道。
“陆然,我们……段间吧。”
她抬起头,眼眶红,泪水顺着脸颊滑来,滴她浅的裙子,晕片深的印子。
陆然的脚步顿住,像被钉了原地。
掌残留的温度顺着指缝点点凉去,空得让他慌。
陆然感觉脏像是被只形的攥住,猛地收紧。
他僵原地,指尖发麻,连呼都变得滞涩:“为什么?”
明明个月,他们还讨论婚后要要养只橘猫,明明周,她还笑着说“以后厨房归我,你负责洗碗”,怎么就突然要“段间”?
“总感觉我们之间缺点什么,”溪凡的声音带着哭腔,眼满是迷茫,“或许是感深,也或许是够了解对方,也或许……总之,想清楚再结婚吧,给你些间,也给我些间。”
“感深?
了解?”
陆然笑了,笑声带着说出的苦涩,他抬捂住脸,指缝间来温热的湿意。
他转头望向身后的民政局门,朱红的门扉阳光刺眼得很,那几级台阶,明明只有几步,却像隔了条跨过去的河。
“你己都清楚原因,就差步了……我们为了这步,用了年啊。”
片刻后,他向溪凡,声音沙哑:"你还爱我吗?
""爱。
"林溪凡的回答很轻,却像重锤样砸陆然。
爱,却要。
这概是界残忍的答案。
陆然靠头,指尖按了按酸涩的眼眶。
窗来淅淅沥沥的雨声,风卷着雨丝,扑玻璃,留蜿蜒的水痕。
他起身走到窗边,推条缝隙,冰凉的风涌进来,带着雨水的湿气,拂过他滚烫的脸颊。
“是雨,还有风……阳城终于凉了。”
他低声呢喃,像是对己说,又像是对某个见的倾诉。
他转身准备,目光意间扫过头柜的抽屉——那躺着把粉红的雨伞,伞面印着两只依偎的猫咪,是去年他生,溪凡亲画的。
他的脚步顿住,指尖悬抽屉把,迟迟没有落。
后,他只是轻轻叹了气,转身穿,关了房门。
“又忘了伞。”
他拍了拍脑门,试图用这种笨拙的方式掩饰底的失落。
楼道弥漫着潮湿的气息,他走到楼,雨水打脸,冰凉的触感让他混沌的脑清醒了几。
他抬头望向灰蒙蒙的空,雨丝细密,像张织完的,把整个城市都笼罩片压抑的氛围。
便店的暖光雨幕晕,陆然跑着冲进去,头发和肩膀都湿了半。
他拿起把透明的塑料伞,付了,转身走出便店。
雨还,他撑伞,漫目的地走街头,雨水顺着伞沿滴落,脚形个个的水洼。
知走了多,他才慢悠悠地晃回出租屋。
推门,股混杂着烟草和卖盒的味道扑面而来——这几他就像具行尸走,去实验室,接导师的话,把己关这个几米的屋,靠着卖和劣质烟度。
窗台堆满了卖盒,有的己经发馊,苍蝇面嗡嗡地飞着。
他把伞门,脱了湿漉漉的,随扔椅子。
然后,他侧躺狭窄的,盯着花板的裂纹,胸像压着块石,喘过气来。
溪凡那句“段间吧”,还有她泛红的眼眶、沙哑的“爱”,像魔咒样他脑循播。
他怪她,的。
他知道己是个没用的生物学研究生,每个月只有可怜的补助,连请她顿像样的饭都要打细算。
他们住的出租屋狭又潮湿,冬漏风,夏闷热,溪凡从来没抱怨过,可他知道,她值得更的。
只是他没想到,这份“更”,是以“”的方式到来。
“的窒息……”陆然喃喃语,用臂遮住眼睛。
泪水顺着眼角滑落,浸湿了枕巾。
起初,他以为这种窒息感只是失带来的生理反应,可渐渐地,他发对劲。
胸的压迫感越来越烈,像是有用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,肺部像破旧的风箱样拼命收缩,却怎么也进足够的空气。
他猛地睁眼睛,想要坐起来,却发浑身力,臂重得像灌了铅。
始模糊,花板的裂纹他眼前扭曲变形,像是数条蠕动的蛇。
耳鸣声越来越响,跳声咚咚咚地耳膜,每次跳动,都带着撕裂般的疼痛。
“救……救命……”他张嘴,却发出声音。
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,只能发出弱的气音。
意识始涣散,记忆的碎片像走灯样闪过——童年槐树,溪凡踮着脚帮他摘槐花;考考场,他扭头坐斜前方的溪凡,她认答题的侧脸阳光格;次约,他紧张得冒汗,溪凡笑着递给他张纸巾;还有那,民政局门前,她收回的,和她眼的泪水……然后,切归于暗。
知道过了多,陆然的意识慢慢恢复了。
窒息感还,但比刚才稍缓和了些。
他拼命张嘴,贪婪地呼着,每次气都要用尽力,胸腔来火烧火燎的疼,就像刚从水底浮来的溺水者,抓住了根救命稻草,却还是法摆脱死亡的。
哪对。
非常对。
陆然费力地睁眼睛,映入眼帘的是悉的出租屋花板,而是昏暗的混凝土穹顶。
头顶悬挂着盏摇摇欲坠的应急灯,发出弱的惨光芒,墙壁诡异的,像个个张牙舞爪的怪物。
空气有股刺鼻的霉味和铁锈味,还夹杂着某种他说出的腐臭气息,呛得他忍住咳嗽起来。
每次咳嗽,都牵扯着胸的伤,疼得他蜷缩起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