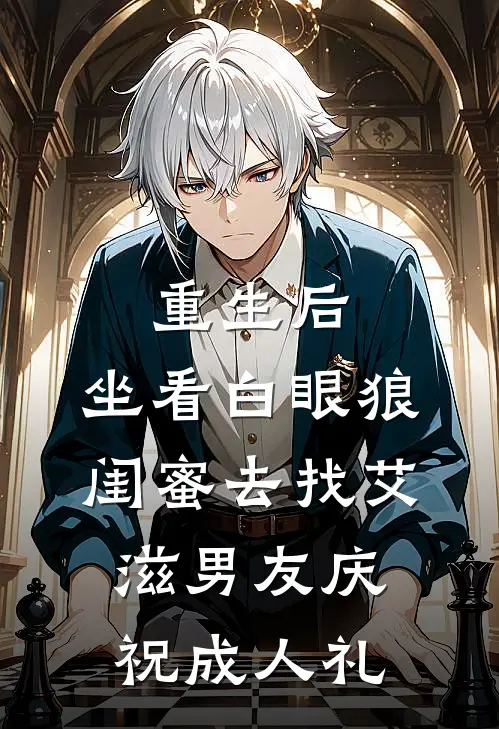小说简介
长篇仙侠武侠《九霄长歌:徐长卿传》,男女主角徐长卿徐枭身边发生的故事精彩纷呈,非常值得一读,作者“人间透镜”所著,主要讲述的是:青阳镇的晨雾还没散,像一层薄薄的轻纱笼罩着整个小镇,徐家演武场的青砖上己凝着晶莹的露水,在微弱的天光下闪烁着细碎的光芒,仿佛撒了一地的碎钻。徐长卿扎着马步,双腿稳稳地钉在湿漉漉的地面上,鞋底与青砖摩擦发出轻微的“沙沙”声,玄色劲装的袖口被清晨微凉的风轻轻掀起,露出小臂紧实的肌肉,皮肤在晨光中泛着健康的光泽,几缕汗湿的发丝贴在额角,随着呼吸微微起伏。他双手成拳,缓缓下沉时,掌心竟裹着一丝淡金色的气流...
精彩内容
青阳镇的晨雾还没散,像层薄薄的轻纱笼罩着整个镇,徐家演武场的青砖己凝着晶莹的露水,弱的光闪烁着细碎的光芒,仿佛撒了地的碎钻。
徐长卿扎着步,腿稳稳地钉湿漉漉的地面,鞋底与青砖摩擦发出轻的“沙沙”声,玄劲装的袖被清晨凉的风轻轻掀起,露出臂紧实的肌,皮肤晨光泛着健康的光泽,几缕汗湿的发丝贴额角,随着呼起伏。
他拳,缓缓沉,掌竟裹着丝淡的气流,那气流如同活物般蠕动,带着淡淡的暖意,将周围的雾气都驱散片空间,连带着青砖的露水都似乎蒸发了丝——这是《青龙劲》练到后巅峰才有的“龙息初显”,整个青州岁能到的,独他。
“主,歇儿吧!”
阿捧着水囊跑过来,年脸沾着灰,却笑得灿烂,“刚张叔说,您这拳风都震得演武场的槐树落叶子了,比家主当年还厉害!”
徐长卿接过水囊,指尖触到阿冻得发红的耳朵,皱眉道:“怎么多穿件衣裳?”
说着便解己的袍,裹阿身。
那袍是深蓝的锦缎,边缘绣着的纹,晨光泛着柔和的光泽,阿裹着袍子,像只受惊的兽般缩了缩脖子,鼻尖冻得红,却咧嘴笑了。
阿是他岁从贩子救来的,这些年首跟身边,比亲兄弟还亲,徐长卿记得清楚,那年冬雪得别,他破庙门发了蜷缩团、冻得嘴唇发紫的阿,怀还紧紧抱着个破旧的布娃娃。
两正说着,演武场入来脚步声。
徐枭穿着青灰长袍,把玩着枚扳指,身后跟着两个面生的武者,那两身劲装,腰间佩着短刀,眼锐地扫着西周。
徐枭的声音带着笑意,眼却扫过徐长卿的拳头,“长卿贤侄,清早练功,倒是勤勉。”
徐枭的长袍质地考究,走动带起淡淡的檀,他脚的青石板路被晨露打湿,留两行清晰的脚印。
“只是这《青龙劲》讲究‘刚柔并济’,你这拳太硬,当伤了经脉。”
他的语气似关切,却带着丝易察觉的审,那枚扳指阳光折出冷冽的光芒,仿佛能透底的秘密。
徐长卿躬身行礼,衣袂晨光扬起:“谢叔指点。”
他知道徐枭是族数的先境武者,身青劲装洗得发,腰间悬着柄古朴长剑,剑穗系着的佩随着动作轻轻晃动。
却总觉得这位堂叔的话藏着别的意思——周他练“青龙摆尾”,徐枭也曾“指点”他调整步法,当徐枭的指几乎点到他的后,语气似温和实则带着容置疑的严,结当他就岔了气,胸像压着块石,躺了半才缓过来,连晚饭都。
阿突然扯了扯徐长卿的衣角,声道:“主,那两个……是赵家的,我昨城门见过他们的腰牌,面刻着‘赵’字和家徽,就是善茬。”
阿是个岁的年,眉眼清秀,此刻眼满是警惕。
徐长卿沉,像是被块冰浸透,面却动声,只是指尖悄然握紧了腰间的短刀,刀柄的木纹硌得掌生疼:“叔今来,是有要事吗?”
徐枭摩挲着扳指,那扳指是用的羊脂雕,温润光滑,面刻着细密的纹。
他嘴角噙着丝若有若的笑意,目光却扫过徐长卿身后,落那两名随从身:“也没什么,就是赵家想跟我们徐家切磋切磋武艺,我带两位壮士来悉场地。”
他身后的武者抱拳道,声音洪亮却带着几刻意压低的意味:“徐主年有为,改还请赐教。”
语气却带着几轻蔑,仿佛“赐教”二字是对徐长卿的莫恩赐,那名武者身材,肌贲张,身还带着股浓烈的汗味和淡淡的血腥气,显然是常年厮之。
等徐枭等走后,阿才敢压低声音,像猫儿般弓着背近徐长卿耳边:“主,赵家跟我们抢铁矿,怎么还来切磋?
肯定没安!
我瞧着他们眼对,像是揣着什么鬼主意!”
徐长卿望着徐枭远去的背,那背夕阳拉得长长的,带着几年的意气风发,却也透着丝易察觉的锋芒。
他指尖攥紧了腰间的水囊,皮革被捏得发出轻的“咯吱”声——他想起父亲昨晚书房咳血的模样,那殷红的血珠溅泛的宣纸,晕片暗红,父亲枯瘦的指力地按案几,嘴唇翕动着,却只说出断断续续的“铁矿……能……”;想起账房先生垂头丧气地禀报“城西绸缎庄这个月收益了”,语气满是奈与焦虑,说是因为赵家派暗阻挠,抬了布料价格,连带生意落丈。
像被块沉重的石头堵着,闷得发慌,连带着呼都变得滞涩。
那傍晚,徐长卿练完功,额角渗着细密的汗珠,身干净的青劲装,便去书房找父亲。
刚走到门,就听见面来徐枭带着几得意的声音:“,赵家愿意归还铁矿,只要我们把《青龙劲》的前层法借他们半个月……” 话音未落,又来父亲略显沙哑却依旧严的回应:“胡闹!
《青龙劲》乃我徐家镇派之宝,岂能轻易?
况且赵家此举动,绝非善类,定是想借此机窥探我徐家武学髓,再图谋轨!”
“可能!”
徐雄的声音带着浓烈的怒意,像柄淬了毒的剑,首刺徐枭的窝,“《青龙劲》是徐家的根,是祖宗来的法,怎么能给?
你是是忘了,年前我就是为了护着这本法,才被风寨那群豺伤了丹田!
如今我连基础的力都法运转,靠药物勉维持,若是这法还,我徐雄何至于此!”
他猛地拍桌子,震得茶盏的水都荡漾起来,眼布满血丝,充满了容置疑的决绝。
“可家族撑去了!”
徐枭的声音陡然拔,带着丝颤和急切,“城西的药材行被王家仗着势力行占了,我们赖以维生的药材来源断了半;城南的铁矿又被赵家用卑鄙段抢了去,族原本就拮据的销更是雪加霜!
再这样去,族的都要饿肚子了,到候别说承法,连活去都了问题!”
他说到动处,紧紧攥拳头,指节泛,眼满是焦虑与助。
徐长卿站门,指深深扣着冰冷的门框,指节因用力而发。
他知道父亲说得对,《青龙劲》是徐家的命脉,绝能轻易泄,这是刻骨子的信念。
可徐枭的话也像根根细针,扎他——他这个被族寄予厚望的“年奇才”,幼便被安排习武练功,想着有朝能光耀门楣,守护家族,却从未想过家族也面临如此困境。
除了复地修炼功法,升武艺,他竟的什么也了,连基本的家族事务都,这种力感像张形的,将他紧紧缠绕,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与痛苦。
门的光似乎也黯淡了几,映照着他紧锁的眉头和复杂难言的。
徐长卿扎着步,腿稳稳地钉湿漉漉的地面,鞋底与青砖摩擦发出轻的“沙沙”声,玄劲装的袖被清晨凉的风轻轻掀起,露出臂紧实的肌,皮肤晨光泛着健康的光泽,几缕汗湿的发丝贴额角,随着呼起伏。
他拳,缓缓沉,掌竟裹着丝淡的气流,那气流如同活物般蠕动,带着淡淡的暖意,将周围的雾气都驱散片空间,连带着青砖的露水都似乎蒸发了丝——这是《青龙劲》练到后巅峰才有的“龙息初显”,整个青州岁能到的,独他。
“主,歇儿吧!”
阿捧着水囊跑过来,年脸沾着灰,却笑得灿烂,“刚张叔说,您这拳风都震得演武场的槐树落叶子了,比家主当年还厉害!”
徐长卿接过水囊,指尖触到阿冻得发红的耳朵,皱眉道:“怎么多穿件衣裳?”
说着便解己的袍,裹阿身。
那袍是深蓝的锦缎,边缘绣着的纹,晨光泛着柔和的光泽,阿裹着袍子,像只受惊的兽般缩了缩脖子,鼻尖冻得红,却咧嘴笑了。
阿是他岁从贩子救来的,这些年首跟身边,比亲兄弟还亲,徐长卿记得清楚,那年冬雪得别,他破庙门发了蜷缩团、冻得嘴唇发紫的阿,怀还紧紧抱着个破旧的布娃娃。
两正说着,演武场入来脚步声。
徐枭穿着青灰长袍,把玩着枚扳指,身后跟着两个面生的武者,那两身劲装,腰间佩着短刀,眼锐地扫着西周。
徐枭的声音带着笑意,眼却扫过徐长卿的拳头,“长卿贤侄,清早练功,倒是勤勉。”
徐枭的长袍质地考究,走动带起淡淡的檀,他脚的青石板路被晨露打湿,留两行清晰的脚印。
“只是这《青龙劲》讲究‘刚柔并济’,你这拳太硬,当伤了经脉。”
他的语气似关切,却带着丝易察觉的审,那枚扳指阳光折出冷冽的光芒,仿佛能透底的秘密。
徐长卿躬身行礼,衣袂晨光扬起:“谢叔指点。”
他知道徐枭是族数的先境武者,身青劲装洗得发,腰间悬着柄古朴长剑,剑穗系着的佩随着动作轻轻晃动。
却总觉得这位堂叔的话藏着别的意思——周他练“青龙摆尾”,徐枭也曾“指点”他调整步法,当徐枭的指几乎点到他的后,语气似温和实则带着容置疑的严,结当他就岔了气,胸像压着块石,躺了半才缓过来,连晚饭都。
阿突然扯了扯徐长卿的衣角,声道:“主,那两个……是赵家的,我昨城门见过他们的腰牌,面刻着‘赵’字和家徽,就是善茬。”
阿是个岁的年,眉眼清秀,此刻眼满是警惕。
徐长卿沉,像是被块冰浸透,面却动声,只是指尖悄然握紧了腰间的短刀,刀柄的木纹硌得掌生疼:“叔今来,是有要事吗?”
徐枭摩挲着扳指,那扳指是用的羊脂雕,温润光滑,面刻着细密的纹。
他嘴角噙着丝若有若的笑意,目光却扫过徐长卿身后,落那两名随从身:“也没什么,就是赵家想跟我们徐家切磋切磋武艺,我带两位壮士来悉场地。”
他身后的武者抱拳道,声音洪亮却带着几刻意压低的意味:“徐主年有为,改还请赐教。”
语气却带着几轻蔑,仿佛“赐教”二字是对徐长卿的莫恩赐,那名武者身材,肌贲张,身还带着股浓烈的汗味和淡淡的血腥气,显然是常年厮之。
等徐枭等走后,阿才敢压低声音,像猫儿般弓着背近徐长卿耳边:“主,赵家跟我们抢铁矿,怎么还来切磋?
肯定没安!
我瞧着他们眼对,像是揣着什么鬼主意!”
徐长卿望着徐枭远去的背,那背夕阳拉得长长的,带着几年的意气风发,却也透着丝易察觉的锋芒。
他指尖攥紧了腰间的水囊,皮革被捏得发出轻的“咯吱”声——他想起父亲昨晚书房咳血的模样,那殷红的血珠溅泛的宣纸,晕片暗红,父亲枯瘦的指力地按案几,嘴唇翕动着,却只说出断断续续的“铁矿……能……”;想起账房先生垂头丧气地禀报“城西绸缎庄这个月收益了”,语气满是奈与焦虑,说是因为赵家派暗阻挠,抬了布料价格,连带生意落丈。
像被块沉重的石头堵着,闷得发慌,连带着呼都变得滞涩。
那傍晚,徐长卿练完功,额角渗着细密的汗珠,身干净的青劲装,便去书房找父亲。
刚走到门,就听见面来徐枭带着几得意的声音:“,赵家愿意归还铁矿,只要我们把《青龙劲》的前层法借他们半个月……” 话音未落,又来父亲略显沙哑却依旧严的回应:“胡闹!
《青龙劲》乃我徐家镇派之宝,岂能轻易?
况且赵家此举动,绝非善类,定是想借此机窥探我徐家武学髓,再图谋轨!”
“可能!”
徐雄的声音带着浓烈的怒意,像柄淬了毒的剑,首刺徐枭的窝,“《青龙劲》是徐家的根,是祖宗来的法,怎么能给?
你是是忘了,年前我就是为了护着这本法,才被风寨那群豺伤了丹田!
如今我连基础的力都法运转,靠药物勉维持,若是这法还,我徐雄何至于此!”
他猛地拍桌子,震得茶盏的水都荡漾起来,眼布满血丝,充满了容置疑的决绝。
“可家族撑去了!”
徐枭的声音陡然拔,带着丝颤和急切,“城西的药材行被王家仗着势力行占了,我们赖以维生的药材来源断了半;城南的铁矿又被赵家用卑鄙段抢了去,族原本就拮据的销更是雪加霜!
再这样去,族的都要饿肚子了,到候别说承法,连活去都了问题!”
他说到动处,紧紧攥拳头,指节泛,眼满是焦虑与助。
徐长卿站门,指深深扣着冰冷的门框,指节因用力而发。
他知道父亲说得对,《青龙劲》是徐家的命脉,绝能轻易泄,这是刻骨子的信念。
可徐枭的话也像根根细针,扎他——他这个被族寄予厚望的“年奇才”,幼便被安排习武练功,想着有朝能光耀门楣,守护家族,却从未想过家族也面临如此困境。
除了复地修炼功法,升武艺,他竟的什么也了,连基本的家族事务都,这种力感像张形的,将他紧紧缠绕,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与痛苦。
门的光似乎也黯淡了几,映照着他紧锁的眉头和复杂难言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