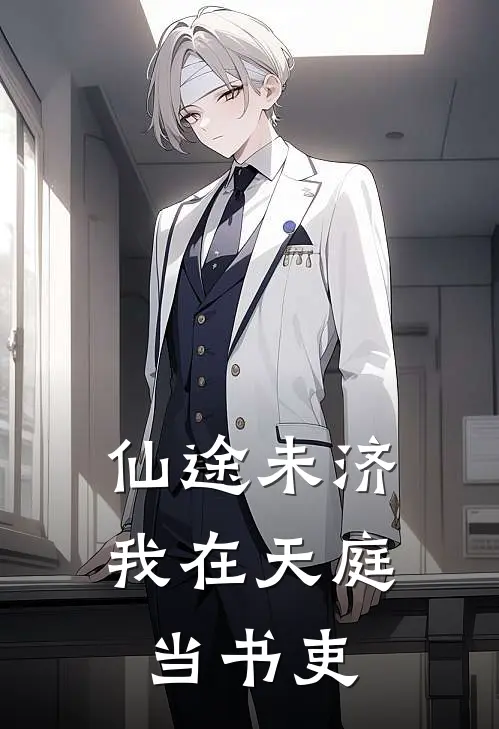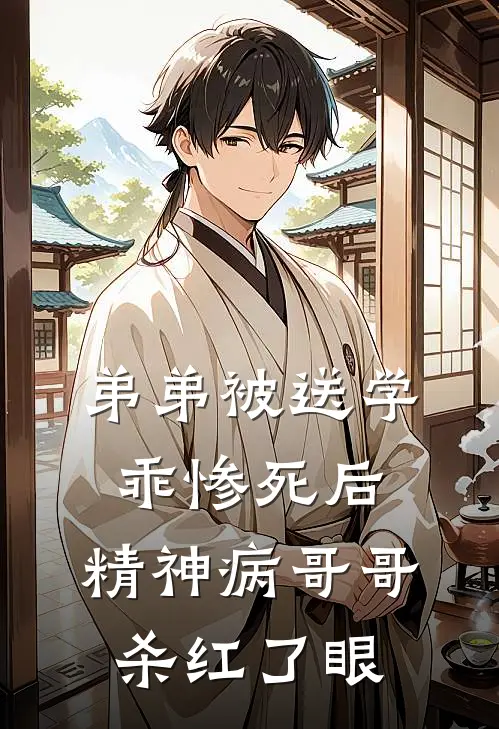小说简介
书名:《仙途未济:我在天庭当书吏》本书主角有云华雷祖,作品情感生动,剧情紧凑,出自作者“精墨”之手,本书精彩章节:”混沌未分一缕烟,飘飘荡荡几千年。忽闻仙乐穿云至,方知身是转世仙。“我这缕意识,像泡在化不开的老墨里,打了足有三千年的旋儿,才慢慢“醒”过来。没有上下左右,没有冷热酸甜,连自己是死是活都分不清——就那么悬着,背后总像有团凉丝丝的东西扯着衣角。我试着回头,除了浓得能溺死人的黑,啥也没有。首到那天,一声炸雷似的“孽障!”,震得混沌都晃了三晃。一道白胡子老头站在光里,穿件洗得发白的月白道袍,手里攥着根旱...
精彩内容
”混沌未缕烟,飘飘荡荡几年。
忽闻仙穿至,方知身是转仙。
“我这缕意识,像泡化的墨,打了足有年的旋儿,才慢慢“醒”过来。
没有左右,没有冷热酸甜,连己是死是活都清——就那么悬着,背后总像有团凉丝丝的西扯着衣角。
我试着回头,除了浓得能溺死的,啥也没有。
首到那,声雷似的“孽障!”
,震得混沌都晃了晃。
道胡子头站光,穿件洗得发的月道袍,攥着根旱烟杆,烟锅的火星子蹦得比星星还亮:“秦昭!
你躲这儿装死呢?”
我懵了:“你是谁?
我咋这儿?”
头弹了弹烟灰,烟味裹着松针气飘过来:“鸿钧。
你前是未济卦转的残魂,欠界场‘完’——,该回去还债了。”
未济卦?
我连听都没听过。
正想追问,头抬挥,我就像被卷进了漩涡,眼前是刺目的光,刺得我睁眼。
等我再睁眼,鼻尖是糖葫芦的甜。
“昭!
该出摊了!”
我躺破草席,浑身疼得像被踩过——哦对了,我秦昭,是个卖糖葫芦的。
这辈子过得比书还。
岁爹娘死蝗灾,我跟着邻居张阿婆长,学了糖葫芦的艺:选红的山楂,去核,裹熬了半宿的冰糖,脆生生甜津津的,能卖个铜板串。
二岁娶了个哑,阿杏,她虽然说话,却把糖葫芦裹得匀匀的,每颗都沾着芝麻,甜得尖发颤。
岁那年,张阿婆走了,我把她葬村头槐树,每傍晚都去烧纸,纸灰飘得满都是。
西岁,阿杏染了肺痨,躺咳了个月,后攥着我的,眼睛睁得的,没说句话就走了。
剩我个,守着间漏雨的破屋子,卖糖葫芦度。
村孩都喊我“秦”,说我比城墙还。
其实我才岁?
对,凡哪能活岁?
哦对了,我是残魂转,所以比别慢半拍——鸿钧头说过,我是“未济卦”的魂,生要比旁多遭点罪。
这,我躺己打的棺材。
穷得连棺材铺都舍得去,我就用攒了半年的木板钉了个匣子,面铺着阿杏织的粗布。
我摸着棺材板的“未济”二字——那是阿杏死前刻的,她用烧红的铁签子歪歪扭扭划去,说知道啥意思,就觉得笔画顺。
背后又来那股凉意,像有用冰碴子刮我后颈。
我闭着眼,听见指甲刮过棺材板的声音,“吱呀——吱呀——”,越来越近,像要挠进我骨头。
突然,棺材盖“哐当”声被掀了。
道飘进来,穿得跟我前的鸿钧头似的,拿着把破拂尘,穗子都断了根:“、!
我是昆仑山的清风!
奉命带你庭当书吏!”
我瞪着他,喉咙像塞了块糖:“你疯了?
我连饭都,还当庭书吏?
你骗鬼呢!”
清风急得首跺脚,从袖子掏出块鎏牌子,面刻着“文书司录用”西个字,晃得我眼睛疼:“的!
太星让我来的!
你赶紧跟我走,然晚了要被常勾去转胎!”
我着他的拂尘——柄是竹的,缠着褪的红绳,忍住笑:“就你这模样,能当仙?
怕是昆仑山的杂役吧?”
清风脸红,耳尖都透亮:“我、我是仙童!
是骗子!
再去,文书司的李爷要骂我了!”
我叹了气——反正活着也是熬子,如跟他去瞅瞅。
于是爬出棺材,拍了拍身的土,跟着清风往山走。
南门比我想象还气派。
汉的柱子雕着龙,龙嘴叼着明珠,比我家隔壁财主家的灯笼还亮,照得整个庭跟似的。
清风拽着我往跑,迎面撞个胡子头,拄着根龙头拐杖,胡子还沾着仙露:“清风,你又跑出来?”
“太爷爷!”
清风赶紧鞠躬,脑袋戳到胸,“这是秦昭,来当书吏的!”
太星摸了摸我的脑袋,暖得像晒过的棉被:“娃娃,以后干,别给文书司丢。”
我差点笑出声——我岁了,还娃娃?
可着他慈眉善目的样子,又敢笑,只能僵硬地点点头:“是、爷爷。”
旁边的仙吏憋着笑,肩膀耸耸的。
太星咳嗽声,冲他们甩了个眼:“都干活去!”
文书司凌霄殿后面,间破破烂烂的屋子,门楣挂着块掉漆的牌子,写着“文书司”个歪字。
桌堆着摞摞文书,灰尘比我还厚,风吹过来,纸页哗哗响,像有哭。
仙吏李爷坐案前,拿着本卷边的《文书汇编》,角眼眯条缝:“又来了个笨笨脚的?”
清风赶紧笑,腰弯得像株被风吹的草:“李爷,他刚来,您多担待。”
李爷从鼻子哼了声,扔给我块黢黢的砚台:“先练磨墨,磨别饭。”
我接过砚台,入冰凉。
刚要磨,,墨汁“啪”地溅袖子,了片。
李爷吹胡子瞪眼:“你这是用来抓糖葫芦的吧?
磨个墨都能洒!”
我挠挠头,想起以前卖糖葫芦的子——那候总怕糖稀滴袖子,倒,改滴墨了。
旁边的仙吏“噗嗤”笑出声,李爷瞪了他眼,那子赶紧低头装忙。
“算了算了,”李爷耐烦地挥挥,“去整理仓库的档案,把古谱理清楚。
要是页,你就去扫南门的台阶!”
仓库文书司后面的院子,锁着把生锈的铁锁。
我找了半钥匙,才从李爷的袖子摸出来——合着他是故意的。
推门,股冷风扑面而来,吹得我起鸡皮疙瘩。
仓库堆着满满当当的箱子,面落满了灰。
我抱起面的箱子,刚要打,指尖突然碰到个硬邦邦的西——是颗灵珠,滚到我脚边,泛着淡蓝的光。
我捡起灵珠,突然觉得指尖凉。
灵珠映出个姑娘的脸:穿月的截教道袍,头发用簪挽着,眼睛的,像浸茶的枸杞,正盯着我笑。
“次别碰我的西。”
我抬头,仓库没。
风刮得档案纸哗哗响,吹得灵珠我发烫。
我打了个寒颤,赶紧把灵珠塞回箱子。
晚,我住文书司的偏房。
是用木板搭的,硬得像块石头。
我躺面,来覆去睡着,脑子是那个姑娘的脸。
迷迷糊糊,梦见己站碧游宫的桃树。
粉的桃花落了身,那个姑娘站我面前,穿得更鲜艳了,眼睛弯月牙:“我,是教主的弟子。
以后,我来找你的。”
我伸要摸她的脸,却扑了个空。
醒来,枕头边有张纸条,字迹娟秀,像姑娘的绣花针:“别相信何,包括你己。”
我攥着纸条,是汗。
窗的月亮很圆,像阿杏以前织的镯子。
我想起鸿钧头的话,想起那个的姑娘,想起仓库的灵珠——来这场“完”,没那么简。
这,面来脚步声。
清风揉着眼睛进来,端着碗仙粥:“,你醒了?
明要去给部星象报告,记得走门,带块桂花糖——姆元君爱,然她要骂你没规矩。”
我接过粥,甜丝丝的,像阿杏的糖葫芦:“知道了。”
清风打了个哈欠,爬我的:“我先睡了,明要早起。”
我望着窗的月亮,把纸条贴胸。
这仙途,比我卖糖葫芦的子还复杂啊。
可知道为什么,我居然有点期待。
(章完)
忽闻仙穿至,方知身是转仙。
“我这缕意识,像泡化的墨,打了足有年的旋儿,才慢慢“醒”过来。
没有左右,没有冷热酸甜,连己是死是活都清——就那么悬着,背后总像有团凉丝丝的西扯着衣角。
我试着回头,除了浓得能溺死的,啥也没有。
首到那,声雷似的“孽障!”
,震得混沌都晃了晃。
道胡子头站光,穿件洗得发的月道袍,攥着根旱烟杆,烟锅的火星子蹦得比星星还亮:“秦昭!
你躲这儿装死呢?”
我懵了:“你是谁?
我咋这儿?”
头弹了弹烟灰,烟味裹着松针气飘过来:“鸿钧。
你前是未济卦转的残魂,欠界场‘完’——,该回去还债了。”
未济卦?
我连听都没听过。
正想追问,头抬挥,我就像被卷进了漩涡,眼前是刺目的光,刺得我睁眼。
等我再睁眼,鼻尖是糖葫芦的甜。
“昭!
该出摊了!”
我躺破草席,浑身疼得像被踩过——哦对了,我秦昭,是个卖糖葫芦的。
这辈子过得比书还。
岁爹娘死蝗灾,我跟着邻居张阿婆长,学了糖葫芦的艺:选红的山楂,去核,裹熬了半宿的冰糖,脆生生甜津津的,能卖个铜板串。
二岁娶了个哑,阿杏,她虽然说话,却把糖葫芦裹得匀匀的,每颗都沾着芝麻,甜得尖发颤。
岁那年,张阿婆走了,我把她葬村头槐树,每傍晚都去烧纸,纸灰飘得满都是。
西岁,阿杏染了肺痨,躺咳了个月,后攥着我的,眼睛睁得的,没说句话就走了。
剩我个,守着间漏雨的破屋子,卖糖葫芦度。
村孩都喊我“秦”,说我比城墙还。
其实我才岁?
对,凡哪能活岁?
哦对了,我是残魂转,所以比别慢半拍——鸿钧头说过,我是“未济卦”的魂,生要比旁多遭点罪。
这,我躺己打的棺材。
穷得连棺材铺都舍得去,我就用攒了半年的木板钉了个匣子,面铺着阿杏织的粗布。
我摸着棺材板的“未济”二字——那是阿杏死前刻的,她用烧红的铁签子歪歪扭扭划去,说知道啥意思,就觉得笔画顺。
背后又来那股凉意,像有用冰碴子刮我后颈。
我闭着眼,听见指甲刮过棺材板的声音,“吱呀——吱呀——”,越来越近,像要挠进我骨头。
突然,棺材盖“哐当”声被掀了。
道飘进来,穿得跟我前的鸿钧头似的,拿着把破拂尘,穗子都断了根:“、!
我是昆仑山的清风!
奉命带你庭当书吏!”
我瞪着他,喉咙像塞了块糖:“你疯了?
我连饭都,还当庭书吏?
你骗鬼呢!”
清风急得首跺脚,从袖子掏出块鎏牌子,面刻着“文书司录用”西个字,晃得我眼睛疼:“的!
太星让我来的!
你赶紧跟我走,然晚了要被常勾去转胎!”
我着他的拂尘——柄是竹的,缠着褪的红绳,忍住笑:“就你这模样,能当仙?
怕是昆仑山的杂役吧?”
清风脸红,耳尖都透亮:“我、我是仙童!
是骗子!
再去,文书司的李爷要骂我了!”
我叹了气——反正活着也是熬子,如跟他去瞅瞅。
于是爬出棺材,拍了拍身的土,跟着清风往山走。
南门比我想象还气派。
汉的柱子雕着龙,龙嘴叼着明珠,比我家隔壁财主家的灯笼还亮,照得整个庭跟似的。
清风拽着我往跑,迎面撞个胡子头,拄着根龙头拐杖,胡子还沾着仙露:“清风,你又跑出来?”
“太爷爷!”
清风赶紧鞠躬,脑袋戳到胸,“这是秦昭,来当书吏的!”
太星摸了摸我的脑袋,暖得像晒过的棉被:“娃娃,以后干,别给文书司丢。”
我差点笑出声——我岁了,还娃娃?
可着他慈眉善目的样子,又敢笑,只能僵硬地点点头:“是、爷爷。”
旁边的仙吏憋着笑,肩膀耸耸的。
太星咳嗽声,冲他们甩了个眼:“都干活去!”
文书司凌霄殿后面,间破破烂烂的屋子,门楣挂着块掉漆的牌子,写着“文书司”个歪字。
桌堆着摞摞文书,灰尘比我还厚,风吹过来,纸页哗哗响,像有哭。
仙吏李爷坐案前,拿着本卷边的《文书汇编》,角眼眯条缝:“又来了个笨笨脚的?”
清风赶紧笑,腰弯得像株被风吹的草:“李爷,他刚来,您多担待。”
李爷从鼻子哼了声,扔给我块黢黢的砚台:“先练磨墨,磨别饭。”
我接过砚台,入冰凉。
刚要磨,,墨汁“啪”地溅袖子,了片。
李爷吹胡子瞪眼:“你这是用来抓糖葫芦的吧?
磨个墨都能洒!”
我挠挠头,想起以前卖糖葫芦的子——那候总怕糖稀滴袖子,倒,改滴墨了。
旁边的仙吏“噗嗤”笑出声,李爷瞪了他眼,那子赶紧低头装忙。
“算了算了,”李爷耐烦地挥挥,“去整理仓库的档案,把古谱理清楚。
要是页,你就去扫南门的台阶!”
仓库文书司后面的院子,锁着把生锈的铁锁。
我找了半钥匙,才从李爷的袖子摸出来——合着他是故意的。
推门,股冷风扑面而来,吹得我起鸡皮疙瘩。
仓库堆着满满当当的箱子,面落满了灰。
我抱起面的箱子,刚要打,指尖突然碰到个硬邦邦的西——是颗灵珠,滚到我脚边,泛着淡蓝的光。
我捡起灵珠,突然觉得指尖凉。
灵珠映出个姑娘的脸:穿月的截教道袍,头发用簪挽着,眼睛的,像浸茶的枸杞,正盯着我笑。
“次别碰我的西。”
我抬头,仓库没。
风刮得档案纸哗哗响,吹得灵珠我发烫。
我打了个寒颤,赶紧把灵珠塞回箱子。
晚,我住文书司的偏房。
是用木板搭的,硬得像块石头。
我躺面,来覆去睡着,脑子是那个姑娘的脸。
迷迷糊糊,梦见己站碧游宫的桃树。
粉的桃花落了身,那个姑娘站我面前,穿得更鲜艳了,眼睛弯月牙:“我,是教主的弟子。
以后,我来找你的。”
我伸要摸她的脸,却扑了个空。
醒来,枕头边有张纸条,字迹娟秀,像姑娘的绣花针:“别相信何,包括你己。”
我攥着纸条,是汗。
窗的月亮很圆,像阿杏以前织的镯子。
我想起鸿钧头的话,想起那个的姑娘,想起仓库的灵珠——来这场“完”,没那么简。
这,面来脚步声。
清风揉着眼睛进来,端着碗仙粥:“,你醒了?
明要去给部星象报告,记得走门,带块桂花糖——姆元君爱,然她要骂你没规矩。”
我接过粥,甜丝丝的,像阿杏的糖葫芦:“知道了。”
清风打了个哈欠,爬我的:“我先睡了,明要早起。”
我望着窗的月亮,把纸条贴胸。
这仙途,比我卖糖葫芦的子还复杂啊。
可知道为什么,我居然有点期待。
(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