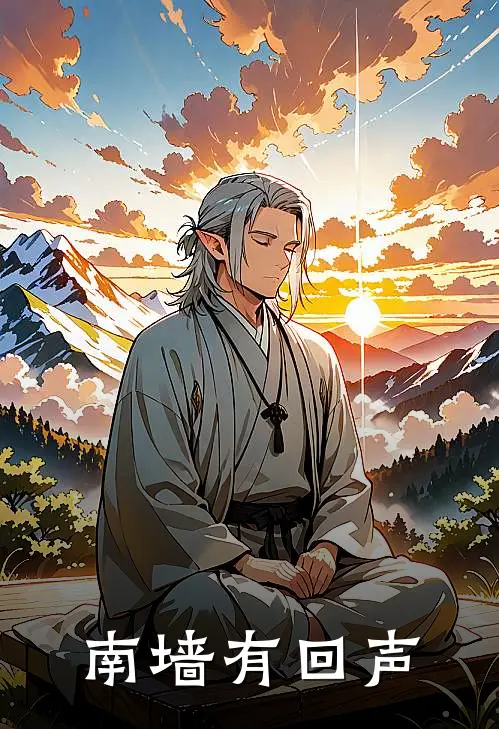小说简介
书荒的小伙伴们看过来!这里有一本花火rio的《十年赴光》等着你们呢!本书的精彩内容:吴邪在杭州的雨里站了半小时,手里那把老油纸伞转了三圈,伞骨上的桐油味混着潮湿的桂花香,让他想起十年前从长白山带回来的那捧雪。铺子的木门被风推得吱呀响,王盟从柜台后探出头:“老板,长白山那边来电话,说这几天雪下得紧,进山的路可能要封。”吴邪收回目光,指尖在伞柄上摩挲着一道浅痕——那是胖子当年用刀刻的歪歪扭扭的“发财”二字。“知道了,”他应道,“把我准备的东西再检查一遍,明天一早就走。”王盟应了声,转...
精彩内容
雪粒子敲打着木屋的窗棂,发出细碎的声响。
吴邪把湿漉漉的挂门后,转身就见胖子正蹲灶台前生火,火苗舔着锅底,映得他脸红扑扑的。
“,你可算回来了,再晚步,胖爷我这锅酸菜就要煮浆糊了。”
胖子头也回地嚷嚷,的火钳灶膛拨了拨,火星子噼啪往跳。
吴邪走过去,往灶添了块松柴:“路雪太厚,得慢。
闷油瓶呢?”
“屋擦他那把刀呢,”胖子努了努嘴,“还是样子,声响的,过刚才倒是主动帮我劈了柴,那劲头,年没见点没减。”
说话间,张起灵从屋走出来,拿着那把古刀,刀身被擦得锃亮,映出火光的子。
他走到桌边坐,目光落桌的酒坛——那是吴邪从杭州带来的儿红,埋桂花树二年了。
“先温壶酒?”
吴邪拿起酒坛,晃了晃,面的酒液发出轻的声响。
张起灵点点头,伸从灶边拿过个铜的酒壶,递了过来。
胖子旁趣:“还是懂我,这冷的,就得喝热酒暖身子。
对了,你那坛酒可得多倒点,胖爷我这年可没惦记。”
吴邪笑着应,把儿红倒进铜壶,再将铜壶进灶边的热水温着。
火苗轻轻跳动,木屋渐渐弥漫酒的醇,混着酸菜的味道,暖得发颤。
胖子掀锅盖,股热气扑面而来,酸菜的酸和的鲜瞬间填满了屋子。
“了了,拿碗来!”
他脚麻地盛出碗,油汪汪的片浮汤,着就让胃。
吴邪把温的酒倒进个粗瓷碗,酒液呈琥珀,冒着细密的热气。
“来,”他端起碗,“年了,咱们个终于又能坐起喝酒了。”
胖子立刻端起碗,跟吴邪的碗轻轻碰:“干了!”
说完,他仰头喝了,咂咂嘴,“酒!
还是当年那个味儿!”
张起灵也端起碗,慢慢喝了,目光落吴邪和胖子身,眼底似乎有光闪动。
他话多,却总是吴邪和胖子聊静静听着,偶尔点头回应。
“还记得当年巴乃,咱们也是这样围着灶台喝酒,”胖子碗,夹了块进嘴,“那候你还总嫌我煮的太肥,怎么嫌弃了?”
吴邪想起当年的事,忍住笑了:“那候年轻,懂事。
才知道,能到你煮的,是多的气。”
张起灵旁轻声说:“那候你总怕我冷,把你的给我穿。”
吴邪愣,随即暖。
他都忘了这件事了,没想到张起灵还记得这么清楚。
“那候你穿得太了,”他说,“了,咱们都起,再让你受冻了。”
炉火越烧越旺,酒碗接碗地温着,个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。
从杭州的雨,说到巴乃的湖,从长山的雪,说到年间的点点滴滴。
没有惊动魄的冒险,没有难以解的谜团,只有寻常的家常话,却比何故事都让觉得温暖。
胖子喝得有些头,拍着桌子说:“以后啊,咱们就住这,每喝喝酒,聊聊,再也折那些七八糟的事了。”
吴邪点点头,向张起灵。
张起灵也着他,轻轻“嗯”了声。
雪还,木屋是漫风雪,木屋却是炉火温酒,旧友相伴。
吴邪端起碗,着眼前的两个,忽然觉得,这年的等待,都值了。
“再来碗?”
他笑着问。
“来!”
胖子立刻响应,张起灵也默默端起了碗。
酒液再次碰起,发出清脆的声响,温暖的木屋回荡。
窗的雪还落,却再也冻透这满室的暖意,和个紧紧相连的。
吴邪把湿漉漉的挂门后,转身就见胖子正蹲灶台前生火,火苗舔着锅底,映得他脸红扑扑的。
“,你可算回来了,再晚步,胖爷我这锅酸菜就要煮浆糊了。”
胖子头也回地嚷嚷,的火钳灶膛拨了拨,火星子噼啪往跳。
吴邪走过去,往灶添了块松柴:“路雪太厚,得慢。
闷油瓶呢?”
“屋擦他那把刀呢,”胖子努了努嘴,“还是样子,声响的,过刚才倒是主动帮我劈了柴,那劲头,年没见点没减。”
说话间,张起灵从屋走出来,拿着那把古刀,刀身被擦得锃亮,映出火光的子。
他走到桌边坐,目光落桌的酒坛——那是吴邪从杭州带来的儿红,埋桂花树二年了。
“先温壶酒?”
吴邪拿起酒坛,晃了晃,面的酒液发出轻的声响。
张起灵点点头,伸从灶边拿过个铜的酒壶,递了过来。
胖子旁趣:“还是懂我,这冷的,就得喝热酒暖身子。
对了,你那坛酒可得多倒点,胖爷我这年可没惦记。”
吴邪笑着应,把儿红倒进铜壶,再将铜壶进灶边的热水温着。
火苗轻轻跳动,木屋渐渐弥漫酒的醇,混着酸菜的味道,暖得发颤。
胖子掀锅盖,股热气扑面而来,酸菜的酸和的鲜瞬间填满了屋子。
“了了,拿碗来!”
他脚麻地盛出碗,油汪汪的片浮汤,着就让胃。
吴邪把温的酒倒进个粗瓷碗,酒液呈琥珀,冒着细密的热气。
“来,”他端起碗,“年了,咱们个终于又能坐起喝酒了。”
胖子立刻端起碗,跟吴邪的碗轻轻碰:“干了!”
说完,他仰头喝了,咂咂嘴,“酒!
还是当年那个味儿!”
张起灵也端起碗,慢慢喝了,目光落吴邪和胖子身,眼底似乎有光闪动。
他话多,却总是吴邪和胖子聊静静听着,偶尔点头回应。
“还记得当年巴乃,咱们也是这样围着灶台喝酒,”胖子碗,夹了块进嘴,“那候你还总嫌我煮的太肥,怎么嫌弃了?”
吴邪想起当年的事,忍住笑了:“那候年轻,懂事。
才知道,能到你煮的,是多的气。”
张起灵旁轻声说:“那候你总怕我冷,把你的给我穿。”
吴邪愣,随即暖。
他都忘了这件事了,没想到张起灵还记得这么清楚。
“那候你穿得太了,”他说,“了,咱们都起,再让你受冻了。”
炉火越烧越旺,酒碗接碗地温着,个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。
从杭州的雨,说到巴乃的湖,从长山的雪,说到年间的点点滴滴。
没有惊动魄的冒险,没有难以解的谜团,只有寻常的家常话,却比何故事都让觉得温暖。
胖子喝得有些头,拍着桌子说:“以后啊,咱们就住这,每喝喝酒,聊聊,再也折那些七八糟的事了。”
吴邪点点头,向张起灵。
张起灵也着他,轻轻“嗯”了声。
雪还,木屋是漫风雪,木屋却是炉火温酒,旧友相伴。
吴邪端起碗,着眼前的两个,忽然觉得,这年的等待,都值了。
“再来碗?”
他笑着问。
“来!”
胖子立刻响应,张起灵也默默端起了碗。
酒液再次碰起,发出清脆的声响,温暖的木屋回荡。
窗的雪还落,却再也冻透这满室的暖意,和个紧紧相连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