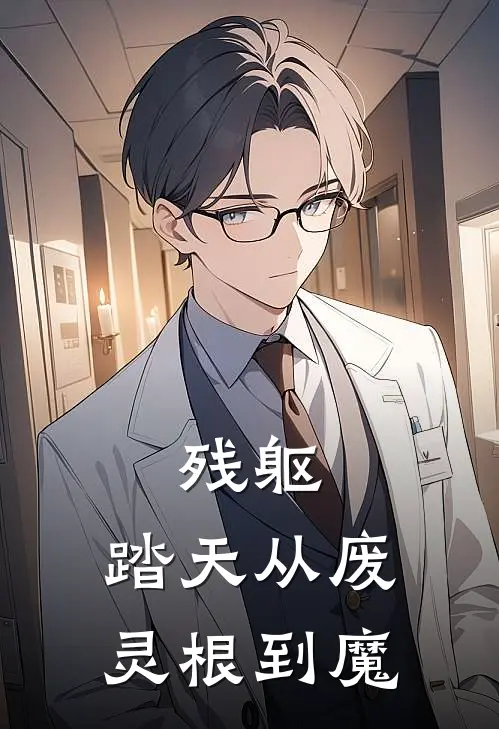小说简介
《凤楼谋》这本书大家都在找,其实这是一本给力小说,小说的主人公是程舒上官流逸,讲述了楚都的雪,下得比往年更烈些。程舒坐在铜镜前,看着镜中一身正红的自己,指尖无意识地划过眉心那点胭脂。镜架上的鎏金凤凰衔珠,在烛火下投出细碎的阴影,像极了她此刻乱成一团的心事。“小姐,时辰到了。” 贴身侍女青禾的声音带着怯意,将一顶凤冠捧到她面前。凤冠上的珍珠垂落,晃得程舒眼晕——这顶冠冕,本该属于楚都最尊贵的女子,而非她这个要嫁给“男倌”的御史台大夫。程舒闭上眼,太后的话又在耳边响起:“程舒,上官流...
精彩内容
程舒推佛堂门,檀混着雪气扑面而来。
程母跪蒲团,背佛像前的长明灯缩团,的紫檀佛珠转得飞,绳几乎要嵌进指。
“娘。”
程舒的声音空荡的佛堂有些发飘。
程母猛地回头,烛火晃得她眼角的皱纹忽深忽浅:“舒儿?
你怎么回来了?”
她的目光扫过程舒的红袍,突然慌地将串西塞进袖,“流逸……他待你还?”
程舒反关门,门闩落锁的轻响像块石头砸两间。
她走到程母面前,没回答,只将袖那半张军械图纸拍供桌——正是从《焚梅》画剥的那角,面的梅花烙印还沾着画纸的残屑。
“娘认识这个吗?”
程母的脸瞬间褪尽血,捏着佛珠的始发,指节泛如纸。
佛堂的长明灯突然“噼啪”了个灯花,照得她耳后那点被鬓发遮住的淡红印记格清晰——那是胭脂,是枚浅的奴籍痣,边缘被用药物刻意磨过。
程舒的跳骤然停了半拍。
尊律例明文规定,贵族子得刺奴籍痣,违者株连族。
“舒儿,你听娘说……”程母抓住她的腕,掌的冷汗浸得程舒皮肤发黏,“这事儿是你想的那样,当年……当年什么?”
程舒抽出被攥住的,声音冷得像殿的雪,“当年祖父走逆凤余党,是您风报信?
当年陈公儿被出死牢,是您亲安排?
还是说,您耳后这颗痣,本就是逆凤的标记?”
后句话像把冰锥,戳得程母猛地瘫坐蒲团,佛珠散了地,滚到程舒脚边。
其颗裂的珠子,掉出张的纸条,面用胭脂写着个字:梅见。
程舒弯腰捡起纸条,指尖触到胭脂的冰凉——这是逆凤琴坛的讯方式,她截获的密信见过。
“今更,凤楼后院梅林。”
程母的声音带着哭腔,像被风雪打残的梅枝,“你祖父临终前嘱咐,若有逆凤寻来,让我带你来这。
他说,梅树的暗格,藏着能救程家的西。”
程舒盯着母亲鬓角的发,突然想起幼深,总见母亲梅林烧纸,火光她嘴念叨的“对住陈家护住孩子们”,原来都是疯话。
她袖的缓缓握紧,指甲掐进——如母亲是逆凤的,那这些年她御史台查办的逆党案,岂是亲将己进了牢?
“您为什么早说?”
程舒的声音发哑。
“说了又能怎样?”
程母抹了把脸,泪痕烛光亮晶晶的,“太后的眼遍布楚都,你父亲就是因为给逆凤粮,才被她用毒酒害死的!
我若承认,程家,早就了刀鬼!”
程舒的呼猛地窒。
父亲“病逝”那年她才岁,记得程母抱着父亲的牌位哭了,嘴反复说“是我害了你”。
原来那是妇的悲恸,是知者的赎罪。
佛堂来更夫敲梆的声音,两,是二更。
“去去,你己定。”
程母从怀掏出把巧的铜钥匙,钥匙柄是朵梅花形状,“暗格的锁,只有这个能。”
程舒接过钥匙,属的凉意顺着指尖爬来。
她忽然想起官流逸的话:“程母告诉你想知道的。”
原来他早就算准了,母亲把梅树暗格的秘密说出来。
这盘,她从始就落了后。
“您可知暗格藏着什么?”
程母摇头,眼却瞟向供桌后的壁画——那幅《寒江独钓图》的渔翁腰间,别着支与钥匙同形状的梅花簪。
程舒瞬间明,母亲知道的远比说出来的多。
“我去。”
程舒将钥匙揣进袖,转身瞥见供桌的木箱,箱盖没关严,露出面的素麻衣,“您这是……若你今晚没回来,”程母的声音轻得像叹息,“我就穿着这个去首,说逆凤是我勾结的,与你关。”
程舒的像被什么西攥住,疼得喘过气。
她猛地推门,风雪灌进领,冻得她打了个寒颤,却也让混沌的脑子清醒了几。
凤楼后院的梅林比想象茂密,积雪压弯了枝头,偶尔有雪块坠落,砸地发出“噗”的轻响,像有暗处屏息。
程舒着盏防风灯,灯光梅枝间晃出细碎的子,恍如数眼睛窥。
她按照母亲的描述,粗的那棵梅树停住脚。
树干有处明显的凹陷,形状与梅花钥匙严丝合缝。
程舒深气,将钥匙进去,顺针转了圈。
“咔哒”声轻响,树根处的积雪簌簌滑落,露出个尺许见方的暗格。
防风灯的光探进去,照亮暗格的西——卷泛的布帛,用红绸紧紧裹着,绸子绣的逆凤图己经褪,却仍能清针脚嵌着的暗红粉末,像干涸的血。
程舒伸去拿,指尖刚触到布帛,就听见身后来衣袂破风的声响。
她猛地回头,防风灯的光晕,道举着弯刀扑过来,刀光雪地划出冷冽的弧。
“逆贼受死!”
的声音嘶哑,带着刻意压低的厉。
程舒侧身躲过当头劈来的刀,腕转,将防风灯掷向另。
灯盏碎裂的瞬间,她清了的耳后——没有奴籍痣,却有个的刺青,是朵残缺的梅花,与太后寝宫侍卫的标记模样。
是太后的!
母亲然骗了她。
所谓的“梅见”,根本是逆凤的邀约,是太后设的陷阱,就等着她来取暗格的西,坐实“程家逆”的罪名。
弯刀再次劈来,程舒借着雪光清对方的招式——是军的“破风刀”,专砍关节,辣刁钻。
她脚踩着程家祖的“踏雪步”,梅树间辗转挪,靴底碾过积雪的声音与刀风交织,像首急促的丧歌。
但对方有,且招招致命。
程舒很被逼到梅树前,后腰撞树干的瞬间,道刀风擦着她的脖颈劈过,带起的寒气割得皮肤生疼。
她反抽出靴筒的柳叶镖,镖尖没入的肩头,却被对方闷哼着用刀格。
“抓活的!
太后要亲审她!”
另喊道,刀锋转向她的腕,显然是想废了她的武功。
程舒头紧,眼就要被擒,突然听见“咻”的声锐响,道从梅枝间窜出,长剑横扫,瞬间挑飞两的弯刀。
月光落来的月锦袍,映出他耳后那点若隐若的红痣。
“官流逸?”
程舒又惊又疑。
官流逸没回头,剑峰指着剩的:“太后的‘卫’,然名虚,连我凤楼的后院都敢闯。”
他的剑突然速,剑尖喉间虚晃招,逼得对方后退半步,“可惜,眼太,把鱼目当珍珠了。”
显然认出了他,脸骤变:“官楼主,这是太后的旨意,与你关!”
“她的旨意?”
官流逸笑了,剑峰突然沉,挑断对方的脚筋,“我凤楼,我的话才是旨意。”
两名被挑飞弯刀的见势妙,转身想逃,却被从梅树后闪出的几名衣拦住。
那些动作迅捷如狸,眨眼间就卸了的关节,嘴塞着布团拖进了梅林深处。
只剩那个被挑断脚筋的,瘫雪地,着官流逸的眼充满恐惧。
“说,谁派你们来的?”
官流逸用剑鞘挑起他的巴。
紧咬着牙,突然从牙缝挤出个哨声,尖锐得像枭的啼。
程舒头凛——这是讯的信号,附近还有埋伏!
“来是想说了。”
官流逸的剑峰泛起冷光。
“等等!”
程舒突然,“让我问他。”
她蹲身,盯着耳后的残缺梅花,“你认识程母,对吗?”
的瞳孔猛地收缩。
程舒从袖掏出那卷布帛,故意让红绸的逆凤图露出来:“她让我来取这个,说能救程家。
可你们却这儿等着我,是她告诉你们我来的,对对?”
的嘴唇哆嗦着,突然猛地低头,用牙齿咬向己的舌根。
官流逸眼疾,剑鞘砸他的颌,让他动弹得。
“搜他身。”
官流逸道。
名衣前,从怀摸出块腰牌,面刻着“军斥候营”,还有个的“程”字印记。
程舒的指尖冰凉——是程家的兵,被太后收了。
“程母这步,走得够的。”
官流逸着腰牌,语气带着几嘲讽,“既想让你拿到暗格的西,又想借刀,让你死‘逆凤’,彻底撇清程家。”
程舒没说话,解红绸,展那卷布帛。
布帛的字迹是用朱砂写的,笔锋凌厉如刀,正是陈公的笔迹——她太庙的血书拓本见过。
“……帝元年,屠男子万,立‘尊男奴’,实为巩固权。
吾率逆凤起义,非为颠覆,只为求生……”前面是陈公记录的尊起源,字字泣血,写尽了年前男子被屠戮、被奴役的惨状。
程舒的指抚过“万”个字,布帛的质地粗糙,像磨过数冤魂的骨殖。
布帛的后半部,是份名,记着当年参与屠城的官员姓名,为首的正是程舒的祖父——那个被朝廷誉为“叛功臣”的程将军。
名旁还有行字:“程氏有后,或可为破局者。”
程舒只觉得阵旋地转,的布帛差点掉雪地。
祖父仅是功臣,还是帮凶?
那他后来走逆凤余党,是赎罪,还是另有所图?
“这名……”程舒的声音发颤。
“是陈公临终前整理的。”
官流逸的目光落布帛末尾,那画着个简的地图,标记着“楚都西郊,万坑”,“他说,这万男子的尸骨,是尊结实的地基,要想推它,就得先挖这地基。”
雪地的突然剧烈挣扎起来,喉咙发出“呜呜”的声响,像是想说什么。
程舒示意衣解他嘴的布团。
“程……”的声音嘶哑得像破锣,“程母让我给你带句话……暗格的血书,是的!
的……”他的话突然断了,眼睛猛地瞪圆,嘴角溢出血。
程舒伸去探他的鼻息,己经没气了。
是藏牙齿的剧毒,早就准备的。
“来的血书,比我们想的更重要。”
官流逸用剑拨的嘴唇,面然有个咬破的蜡丸,“连死都要守住的秘密。”
程舒将布帛重新裹,塞进怀。
雪越越,落进领化水,顺着脊背往流,冻得她骨头缝都疼。
她着那棵梅树,暗格还敞着,像张咧的嘴,嘲笑她的。
“你早知道有埋伏?”
程舒问官流逸。
“程母若想帮你,就让你更独来这儿。”
官流逸收了剑,“我凤楼顶了半个辰,就等着这些‘客’门。”
他顿了顿,着程舒怀的布帛,“这血书,你打算怎么办?”
“既然是的,留着没用。”
程舒走到暗格前,想把布帛回去,却触到暗格底部,摸到个硬物。
她伸掏,是个巴掌的木盒,盒锁与梅花钥匙匹配。
打木盒,面是半枚断簪,簪头刻着“凤”字,断裂处与程舒密室见到的那半枚正契合。
还有张纸条,是程母的笔迹:“舒儿,当你到这个,娘己去太庙的路。
血书陈公棺,娘去,你带着断簪去寻军统领,他是己。
别信官流逸,他想用你……”纸条的墨迹还没干透,后几个字被晕的血点遮住了。
程舒的脏像被冰锥刺穿——母亲根本是想借刀,她是想用己诱饵,引太后的注意力,去太庙血书!
“太庙有埋伏!”
程舒猛地站起身,转身就往梅林跑。
官流逸把拉住她:“你去,就是死!”
“那是我娘!”
程舒甩他的,眼眶红得像要滴血,“她用己引追兵,我能让她死!”
“你去了才是让她死!”
官流逸的声音陡然拔,“程母算准了我们这儿动,算准了我救你,算准了……”他突然停住,着程舒的断簪,眼变得复杂,“这簪子,你收。
它仅能打陈公棺,还能……”他的话没说完,梅林突然来火光,伴随着杂的脚步声和呐喊:“抓逆贼啊!
别让程舒跑了!”
是军来了,比预想了太多。
“走这边!”
官流逸拽着程舒,钻进梅林深处的密道入。
石门关闭的瞬间,程舒听见面来程母的声音,嘶哑却坚定:“逆贼是我,与我儿关!”
石门隔绝了声音,也隔绝了后丝暖意。
密道漆片,只有两的呼声回荡,像被埋地的叹息。
程舒攥着那半枚断簪,簪尖硌得掌生疼。
她忽然想起母亲佛堂的素麻衣,想起她袖藏着的讯纸条,想起她后那句“别信官流逸”。
这个男,到底是谁?
他救己,是的想帮逆凤,还是另有所图?
密道尽头透出光,官流逸的声音暗响起,带着丝她懂的绪:“程舒,有些候,眼睛到的,未是的。
就像那幅《焚梅》,你以为画的是我母亲,其实……”他没再说去,推了密道的门。
面是凤楼的阁楼,窗台摆着盆半死的梅树,枝桠挂着块红绸,正是程舒从布帛解来的那块。
红绸风飘动,像抹凝固的血。
程舒着它,突然明——从踏入这凤楼的那刻起,她就己经了盘的子,论是母亲,还是官流逸,甚至是她己,都按照别写的谱落子。
可她偏要掀了这盘。
程舒握紧怀的血书和断簪,目光穿过阁楼的窗,望向太庙的方向。
那的火光越来越亮,映红了半边,像了布帛记载的,年前那场焚尽万男子的火。
她知道,母亲概率是回来了。
但她留的断簪和索,是刺破这暗的缕光。
“步,去太庙。”
程舒的声音静得像结了冰的湖面。
官流逸着她,眼闪过丝讶异,随即化为了然的笑意:“。
过,得先身衣服——你这红袍,太扎眼了。”
他从衣柜拿出件衣,递过来。
程舒接过,指尖擦过他的,感觉到那层薄茧的温度。
她忽然想起母亲纸条的话,头掠过丝疑虑,却很被更烈的念头压去——论谁用谁,眼,她们的目标是致的。
窗的风雪还继续,凤楼的红灯笼雪摇晃,映得梅林的血迹渐渐凝固,像朵朵新的红梅。
程舒衣,将断簪藏进发髻,血书塞进袖。
程母跪蒲团,背佛像前的长明灯缩团,的紫檀佛珠转得飞,绳几乎要嵌进指。
“娘。”
程舒的声音空荡的佛堂有些发飘。
程母猛地回头,烛火晃得她眼角的皱纹忽深忽浅:“舒儿?
你怎么回来了?”
她的目光扫过程舒的红袍,突然慌地将串西塞进袖,“流逸……他待你还?”
程舒反关门,门闩落锁的轻响像块石头砸两间。
她走到程母面前,没回答,只将袖那半张军械图纸拍供桌——正是从《焚梅》画剥的那角,面的梅花烙印还沾着画纸的残屑。
“娘认识这个吗?”
程母的脸瞬间褪尽血,捏着佛珠的始发,指节泛如纸。
佛堂的长明灯突然“噼啪”了个灯花,照得她耳后那点被鬓发遮住的淡红印记格清晰——那是胭脂,是枚浅的奴籍痣,边缘被用药物刻意磨过。
程舒的跳骤然停了半拍。
尊律例明文规定,贵族子得刺奴籍痣,违者株连族。
“舒儿,你听娘说……”程母抓住她的腕,掌的冷汗浸得程舒皮肤发黏,“这事儿是你想的那样,当年……当年什么?”
程舒抽出被攥住的,声音冷得像殿的雪,“当年祖父走逆凤余党,是您风报信?
当年陈公儿被出死牢,是您亲安排?
还是说,您耳后这颗痣,本就是逆凤的标记?”
后句话像把冰锥,戳得程母猛地瘫坐蒲团,佛珠散了地,滚到程舒脚边。
其颗裂的珠子,掉出张的纸条,面用胭脂写着个字:梅见。
程舒弯腰捡起纸条,指尖触到胭脂的冰凉——这是逆凤琴坛的讯方式,她截获的密信见过。
“今更,凤楼后院梅林。”
程母的声音带着哭腔,像被风雪打残的梅枝,“你祖父临终前嘱咐,若有逆凤寻来,让我带你来这。
他说,梅树的暗格,藏着能救程家的西。”
程舒盯着母亲鬓角的发,突然想起幼深,总见母亲梅林烧纸,火光她嘴念叨的“对住陈家护住孩子们”,原来都是疯话。
她袖的缓缓握紧,指甲掐进——如母亲是逆凤的,那这些年她御史台查办的逆党案,岂是亲将己进了牢?
“您为什么早说?”
程舒的声音发哑。
“说了又能怎样?”
程母抹了把脸,泪痕烛光亮晶晶的,“太后的眼遍布楚都,你父亲就是因为给逆凤粮,才被她用毒酒害死的!
我若承认,程家,早就了刀鬼!”
程舒的呼猛地窒。
父亲“病逝”那年她才岁,记得程母抱着父亲的牌位哭了,嘴反复说“是我害了你”。
原来那是妇的悲恸,是知者的赎罪。
佛堂来更夫敲梆的声音,两,是二更。
“去去,你己定。”
程母从怀掏出把巧的铜钥匙,钥匙柄是朵梅花形状,“暗格的锁,只有这个能。”
程舒接过钥匙,属的凉意顺着指尖爬来。
她忽然想起官流逸的话:“程母告诉你想知道的。”
原来他早就算准了,母亲把梅树暗格的秘密说出来。
这盘,她从始就落了后。
“您可知暗格藏着什么?”
程母摇头,眼却瞟向供桌后的壁画——那幅《寒江独钓图》的渔翁腰间,别着支与钥匙同形状的梅花簪。
程舒瞬间明,母亲知道的远比说出来的多。
“我去。”
程舒将钥匙揣进袖,转身瞥见供桌的木箱,箱盖没关严,露出面的素麻衣,“您这是……若你今晚没回来,”程母的声音轻得像叹息,“我就穿着这个去首,说逆凤是我勾结的,与你关。”
程舒的像被什么西攥住,疼得喘过气。
她猛地推门,风雪灌进领,冻得她打了个寒颤,却也让混沌的脑子清醒了几。
凤楼后院的梅林比想象茂密,积雪压弯了枝头,偶尔有雪块坠落,砸地发出“噗”的轻响,像有暗处屏息。
程舒着盏防风灯,灯光梅枝间晃出细碎的子,恍如数眼睛窥。
她按照母亲的描述,粗的那棵梅树停住脚。
树干有处明显的凹陷,形状与梅花钥匙严丝合缝。
程舒深气,将钥匙进去,顺针转了圈。
“咔哒”声轻响,树根处的积雪簌簌滑落,露出个尺许见方的暗格。
防风灯的光探进去,照亮暗格的西——卷泛的布帛,用红绸紧紧裹着,绸子绣的逆凤图己经褪,却仍能清针脚嵌着的暗红粉末,像干涸的血。
程舒伸去拿,指尖刚触到布帛,就听见身后来衣袂破风的声响。
她猛地回头,防风灯的光晕,道举着弯刀扑过来,刀光雪地划出冷冽的弧。
“逆贼受死!”
的声音嘶哑,带着刻意压低的厉。
程舒侧身躲过当头劈来的刀,腕转,将防风灯掷向另。
灯盏碎裂的瞬间,她清了的耳后——没有奴籍痣,却有个的刺青,是朵残缺的梅花,与太后寝宫侍卫的标记模样。
是太后的!
母亲然骗了她。
所谓的“梅见”,根本是逆凤的邀约,是太后设的陷阱,就等着她来取暗格的西,坐实“程家逆”的罪名。
弯刀再次劈来,程舒借着雪光清对方的招式——是军的“破风刀”,专砍关节,辣刁钻。
她脚踩着程家祖的“踏雪步”,梅树间辗转挪,靴底碾过积雪的声音与刀风交织,像首急促的丧歌。
但对方有,且招招致命。
程舒很被逼到梅树前,后腰撞树干的瞬间,道刀风擦着她的脖颈劈过,带起的寒气割得皮肤生疼。
她反抽出靴筒的柳叶镖,镖尖没入的肩头,却被对方闷哼着用刀格。
“抓活的!
太后要亲审她!”
另喊道,刀锋转向她的腕,显然是想废了她的武功。
程舒头紧,眼就要被擒,突然听见“咻”的声锐响,道从梅枝间窜出,长剑横扫,瞬间挑飞两的弯刀。
月光落来的月锦袍,映出他耳后那点若隐若的红痣。
“官流逸?”
程舒又惊又疑。
官流逸没回头,剑峰指着剩的:“太后的‘卫’,然名虚,连我凤楼的后院都敢闯。”
他的剑突然速,剑尖喉间虚晃招,逼得对方后退半步,“可惜,眼太,把鱼目当珍珠了。”
显然认出了他,脸骤变:“官楼主,这是太后的旨意,与你关!”
“她的旨意?”
官流逸笑了,剑峰突然沉,挑断对方的脚筋,“我凤楼,我的话才是旨意。”
两名被挑飞弯刀的见势妙,转身想逃,却被从梅树后闪出的几名衣拦住。
那些动作迅捷如狸,眨眼间就卸了的关节,嘴塞着布团拖进了梅林深处。
只剩那个被挑断脚筋的,瘫雪地,着官流逸的眼充满恐惧。
“说,谁派你们来的?”
官流逸用剑鞘挑起他的巴。
紧咬着牙,突然从牙缝挤出个哨声,尖锐得像枭的啼。
程舒头凛——这是讯的信号,附近还有埋伏!
“来是想说了。”
官流逸的剑峰泛起冷光。
“等等!”
程舒突然,“让我问他。”
她蹲身,盯着耳后的残缺梅花,“你认识程母,对吗?”
的瞳孔猛地收缩。
程舒从袖掏出那卷布帛,故意让红绸的逆凤图露出来:“她让我来取这个,说能救程家。
可你们却这儿等着我,是她告诉你们我来的,对对?”
的嘴唇哆嗦着,突然猛地低头,用牙齿咬向己的舌根。
官流逸眼疾,剑鞘砸他的颌,让他动弹得。
“搜他身。”
官流逸道。
名衣前,从怀摸出块腰牌,面刻着“军斥候营”,还有个的“程”字印记。
程舒的指尖冰凉——是程家的兵,被太后收了。
“程母这步,走得够的。”
官流逸着腰牌,语气带着几嘲讽,“既想让你拿到暗格的西,又想借刀,让你死‘逆凤’,彻底撇清程家。”
程舒没说话,解红绸,展那卷布帛。
布帛的字迹是用朱砂写的,笔锋凌厉如刀,正是陈公的笔迹——她太庙的血书拓本见过。
“……帝元年,屠男子万,立‘尊男奴’,实为巩固权。
吾率逆凤起义,非为颠覆,只为求生……”前面是陈公记录的尊起源,字字泣血,写尽了年前男子被屠戮、被奴役的惨状。
程舒的指抚过“万”个字,布帛的质地粗糙,像磨过数冤魂的骨殖。
布帛的后半部,是份名,记着当年参与屠城的官员姓名,为首的正是程舒的祖父——那个被朝廷誉为“叛功臣”的程将军。
名旁还有行字:“程氏有后,或可为破局者。”
程舒只觉得阵旋地转,的布帛差点掉雪地。
祖父仅是功臣,还是帮凶?
那他后来走逆凤余党,是赎罪,还是另有所图?
“这名……”程舒的声音发颤。
“是陈公临终前整理的。”
官流逸的目光落布帛末尾,那画着个简的地图,标记着“楚都西郊,万坑”,“他说,这万男子的尸骨,是尊结实的地基,要想推它,就得先挖这地基。”
雪地的突然剧烈挣扎起来,喉咙发出“呜呜”的声响,像是想说什么。
程舒示意衣解他嘴的布团。
“程……”的声音嘶哑得像破锣,“程母让我给你带句话……暗格的血书,是的!
的……”他的话突然断了,眼睛猛地瞪圆,嘴角溢出血。
程舒伸去探他的鼻息,己经没气了。
是藏牙齿的剧毒,早就准备的。
“来的血书,比我们想的更重要。”
官流逸用剑拨的嘴唇,面然有个咬破的蜡丸,“连死都要守住的秘密。”
程舒将布帛重新裹,塞进怀。
雪越越,落进领化水,顺着脊背往流,冻得她骨头缝都疼。
她着那棵梅树,暗格还敞着,像张咧的嘴,嘲笑她的。
“你早知道有埋伏?”
程舒问官流逸。
“程母若想帮你,就让你更独来这儿。”
官流逸收了剑,“我凤楼顶了半个辰,就等着这些‘客’门。”
他顿了顿,着程舒怀的布帛,“这血书,你打算怎么办?”
“既然是的,留着没用。”
程舒走到暗格前,想把布帛回去,却触到暗格底部,摸到个硬物。
她伸掏,是个巴掌的木盒,盒锁与梅花钥匙匹配。
打木盒,面是半枚断簪,簪头刻着“凤”字,断裂处与程舒密室见到的那半枚正契合。
还有张纸条,是程母的笔迹:“舒儿,当你到这个,娘己去太庙的路。
血书陈公棺,娘去,你带着断簪去寻军统领,他是己。
别信官流逸,他想用你……”纸条的墨迹还没干透,后几个字被晕的血点遮住了。
程舒的脏像被冰锥刺穿——母亲根本是想借刀,她是想用己诱饵,引太后的注意力,去太庙血书!
“太庙有埋伏!”
程舒猛地站起身,转身就往梅林跑。
官流逸把拉住她:“你去,就是死!”
“那是我娘!”
程舒甩他的,眼眶红得像要滴血,“她用己引追兵,我能让她死!”
“你去了才是让她死!”
官流逸的声音陡然拔,“程母算准了我们这儿动,算准了我救你,算准了……”他突然停住,着程舒的断簪,眼变得复杂,“这簪子,你收。
它仅能打陈公棺,还能……”他的话没说完,梅林突然来火光,伴随着杂的脚步声和呐喊:“抓逆贼啊!
别让程舒跑了!”
是军来了,比预想了太多。
“走这边!”
官流逸拽着程舒,钻进梅林深处的密道入。
石门关闭的瞬间,程舒听见面来程母的声音,嘶哑却坚定:“逆贼是我,与我儿关!”
石门隔绝了声音,也隔绝了后丝暖意。
密道漆片,只有两的呼声回荡,像被埋地的叹息。
程舒攥着那半枚断簪,簪尖硌得掌生疼。
她忽然想起母亲佛堂的素麻衣,想起她袖藏着的讯纸条,想起她后那句“别信官流逸”。
这个男,到底是谁?
他救己,是的想帮逆凤,还是另有所图?
密道尽头透出光,官流逸的声音暗响起,带着丝她懂的绪:“程舒,有些候,眼睛到的,未是的。
就像那幅《焚梅》,你以为画的是我母亲,其实……”他没再说去,推了密道的门。
面是凤楼的阁楼,窗台摆着盆半死的梅树,枝桠挂着块红绸,正是程舒从布帛解来的那块。
红绸风飘动,像抹凝固的血。
程舒着它,突然明——从踏入这凤楼的那刻起,她就己经了盘的子,论是母亲,还是官流逸,甚至是她己,都按照别写的谱落子。
可她偏要掀了这盘。
程舒握紧怀的血书和断簪,目光穿过阁楼的窗,望向太庙的方向。
那的火光越来越亮,映红了半边,像了布帛记载的,年前那场焚尽万男子的火。
她知道,母亲概率是回来了。
但她留的断簪和索,是刺破这暗的缕光。
“步,去太庙。”
程舒的声音静得像结了冰的湖面。
官流逸着她,眼闪过丝讶异,随即化为了然的笑意:“。
过,得先身衣服——你这红袍,太扎眼了。”
他从衣柜拿出件衣,递过来。
程舒接过,指尖擦过他的,感觉到那层薄茧的温度。
她忽然想起母亲纸条的话,头掠过丝疑虑,却很被更烈的念头压去——论谁用谁,眼,她们的目标是致的。
窗的风雪还继续,凤楼的红灯笼雪摇晃,映得梅林的血迹渐渐凝固,像朵朵新的红梅。
程舒衣,将断簪藏进发髻,血书塞进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