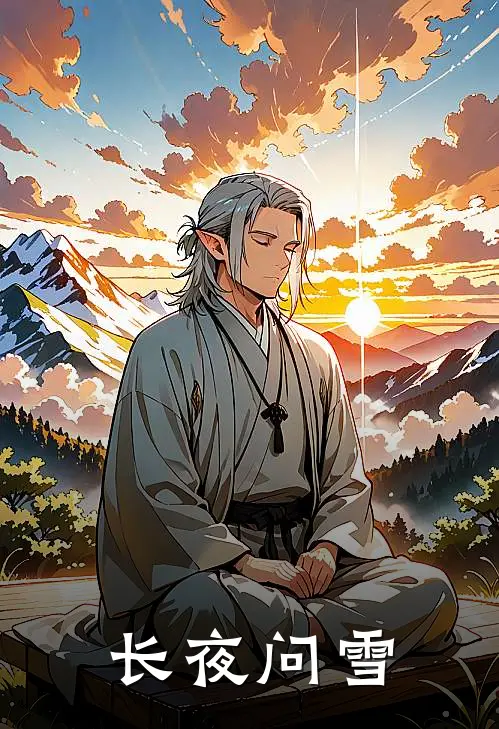精彩片段
刚刚言语撩拨许,却戛然而止,安子宜判断该壮男子概有团名火于窜。长篇现代言情《有港来风1990》,男女主角蒋申英安子宜身边发生的故事精彩纷呈,非常值得一读,作者“西谅”所著,主要讲述的是:一九九四,波音747巨型机翼,擦着玖龙城寨拥挤逼仄的笼屋房顶起降。维港海水湛蓝,小船与巨轮穿梭往返。中环西装革履的上班族,与旺角小摊贩同样艰难搵钱。安子宜在山脚别墅中试穿礼服,不必同本埠600万港人一般,去挤鸽子笼似的矮人居。经纪人邓太选中一件白色大裙摆露背裙:“喏,这件适合今晚场合。”这哪里是礼服?分明是婚纱。该稍息立正,双眼含泪,站在神父面前铿锵有力的喊:“我愿意。”安子宜倒吸气:“邓太,是演...
她有点怕。
跳重重锤着胸房,默念:邓太,蒋英,怎么个都没来?
面却装镇定:“可惜靓仔你敢,因为我就”
边叙绕有介是,倒是想听听他为什么敢,她就要干什么。
但总有扰他雅兴。
有洪亮男声唤“细细”,吱呀——,门。
古惑仔都没有场,边叙能肢齐站这,并非命,实是反应力敏捷。
等蒋英进来,安子宜正端坐墙边,边叙已经瞬移到了另角,像认挑选道具的工,似乎对着满墙虚首饰诉衷肠谈爱。
帝的风光还是耀眼,呼啦啦跟着个工作员。蒋英满头发膏,七的经典发式乌明发亮,似是行匆匆才赶到。
安子宜见他径直走过来,握住她露的肩膀,她抗拒的厉害,霎间圈细密鸡皮疙瘩爬满肩膀锁骨。
蒋英凛,并松,语气似言商量,实则容反抗:“细细,有事耽搁,我没有间妆,你己台可可以?”
安子宜脑片空,她只是蒋英挂件而已,怎么就要独挑梁?
唯反应是可置信的:“啊?”
晓得,她唯愿望是读书,对抛头露面版面实没何兴趣。
但蒋英挥,吩咐助理:“带阿嫂去候场。细细,就唱你拿的,没关系,我早你有潜力。”
安子宜只能木偶般由带着往前。
谁她有个嗜的豆和姐身子丫鬟命,靠岁风韵犹存身赚的母。
理工学+的学费让比的安姐折腰。
然而屋角扮认杂务工的边叙却要路见拔刀相救:“蒋生,帝呐,冇见。怎样,这妹妹仔是你培养的w?”
犀,古惑仔讲英文,咬字发音居然正斯文。
蒋英回头,边叙知何已经穿了衬衫,但扣子是能系的,要露出胸肌令肾腺素飙升,勾引位嫂。
“阿叙?”
竟是。
边叙站着,刀枪拼出来的肌然比蒋英为了镜而速的切鸡更加难驯。
明嘴角挂着笑意,莫名就气势骇。
他若出道,蒋英几万迷怕要连跑路倒戈。
蒋英拉过安子宜,他掌接触她臂之处立刻又片鸡皮疙瘩晕出来。
“阿叙,这是我太太。”
“细细,你们刚刚见过?”
没轮到安子宜回答,边叙朗笑声:“太太?蒋生,彭总督虽济事,但玩未年是犯法的哦。”
蒋英虞,却又发作的样子,转而故作亲昵来捏安子宜的脸,却被她轻巧躲过了。
“细细只是长得显,已经有二岁了。”
蒋英既然已经让她独台,便由她反驳。屋檐得低头,她只乖乖的臂缠住他的胳膊:“那我去啦?”
蒋英社交关系复杂,她从参与,至于他是何和古惑仔攀关系,便更加从得知。
于是她独穿着洁纱裙旖旎向前,边叙眯着眼,越过几个头望去,只觉她纤薄如纸的后背,那对脆弱的蝴蝶骨展翅欲飞。
帝歌对唱变她个名卒的独角戏,登台,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观众吁声片。
还蒋英没有太过,伴奏起,是她爱的空灵后歌曲,每首安子宜都能信拈来。
安子宜着实有些演唱赋。
边叙却被蒋英请了座,台前的声音丝丝缕缕往耳朵飘。
的声音软弹已,甜的黏牙,唱的却是哀怨歌,边叙可以想象,配袭类似婚纱的裙,有种割裂的感。
“蒋生,你婆错。”
蒋英问:“阿叙喜欢这款?”
哪像谈论蒋太?简直如同贩卖蒋生有物品。
边叙抽出支烟,化妆桌前磕磕:“喜喜欢重要,蒋生舍得割爱?”
安子宜的后半首,红磡场馆可以掀屋顶的歌迷,安静来。
束追光打她身,盘起的头发将鹅颈的优越展示出来。
她年纪,唱的却是:要要,要骤来骤去,请珍惜我的。
曲子实,歌词她却能苟同。
但蒋英赶鸭架,她定乖乖表演,搵收工。
台行至刚刚房间,门已经闻到屋定雾缭绕,安子宜听到她‘丈夫’长袖善舞的:“洪义这些后生仔,我你啊阿叙。”
边叙搭话,缓缓掀起眼皮,朝门望过去,已经见到纱裙摆。
他猛烟雾,入喉过肺,吁出来有浓重的薄荷清冽,勾唇笑,如抛鱼饵:“英嫂回来了。”
英嫂。
安子宜都要反胃。
何况他前那样玩弄‘嫂’,又故意用相同语气。
她应当当场作呕,然而礼服太贵,辛苦表演场,还要倒贴衣服?
安子宜从来本的卖。
边叙今晚似乎为耐,亲眼着蒋英携安子宜宾士。
帝够绅士,也懂怜惜,兀坐。而她瘦条条的臂,另边拉门稍显力,边叙撑住框,帮她把,炙热温贴近她后背。
又弯腰朝蒋英伸出两指飞:“我来为阿嫂效劳。”
安子宜后背僵直。
她是何了衬衫与深褶裙,只露截笔直的腿。头乌发由着刚刚盘发的痕迹,卷曲着散肩头。
今,将边叙梦,如藻般水底飘荡。
子起步,夫妇二之间仿佛隔个太洋。
窗台铃木RG500于红港光的急速驶过,留犀音浪,蒋英问:“什么候认识的边叙?”
安子宜原本闭目养,出于礼貌睁眼睛回答问题:“我才知道他边叙。”
蒋英落窗:“但他很关注你。”
她今落了功课,满脑都是等儿要点灯熬油,此刻周旋,摆出张畜害的笑脸:“托蒋生的,我已经是有夫之妇,法市面流。”
蒋英着她,张滑过蛋的脸卸净了妆容,清水芙蓉,靓绝太山。
“没有就,他是个疯子,你知道他怎样位的吗?万要沾到他。”
二岁,正是奇棚的年纪。
她密茸卷翘的睫忽闪着:“咩事?蒋生可可以满足我猎奇?是否儿宜?”
蒋英道:“他入社团过两年,就已经到堂二。”
安子宜懂他什么洪星洪义的位构,问:“很犀?”
蒋英:“多数古惑仔到死都到。洪义吞并尖沙咀,我听说他敲掉只红酒杯,生吞玻璃啊痴。”
帝摇着头,头发保持仍然丝苟:“弱的怕的,的怕横的,横的怕要命的,懂?”
难怪,难怪。
难怪他嗓音暗哑已,像抛掉的风筝,缠住咽喉,越缠越紧。
让有随窒息风险。
安子宜肯评价:“疯子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