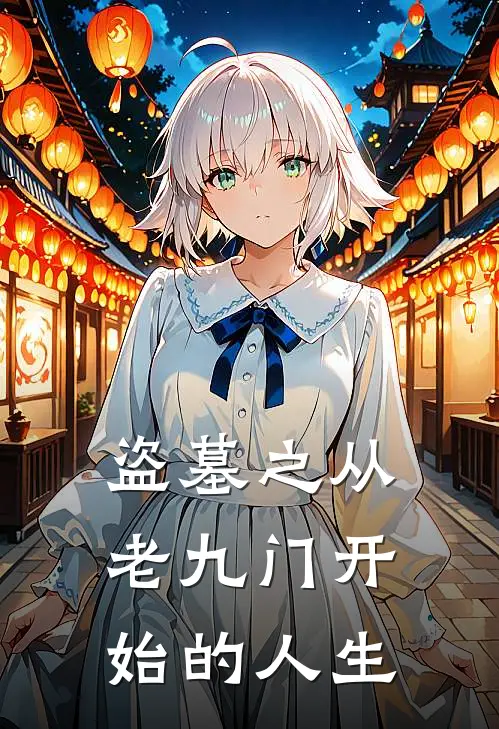精彩片段
雨丝把乡间路泡了烂泥,柳智的二八杠陷泥半寸,链卡进了碎石子。小说叫做《青石板下的钟谜》,是作者管不住嘴的减肥大使的小说,主角为柳智赵小梅。本书精彩片段:青石板路被昨夜的雨浸得发亮,柳智踩着鞋尖避开积水中的槐树叶,鼻腔里满是潮湿的土腥味。这是他回到汀南小城的第三个月——三十岁的人,在上海外贸公司没混出什么名堂,只因在跨国订单里指出了副总小舅子的货损漏洞,转天就收到了调令。没人明说“排挤”,但办公桌抽屉里那盒没拆封的速溶咖啡,如今正压在父母老房客厅的五斗柜下,上面还摆着他小时候用的搪瓷杯,杯沿缺了个小口,是父亲生前补的。他没租房子,父母过世后,这栋带...
他蹲身掏帆布包的螺丝刀,指尖又碰到了那枚铜锁钥匙——从槐树出发前,他意回了趟父母房,除了镜、笔记本和父亲留的旧筒,还顺抓了洗干净的劳保塞进包底,是父亲当年机修厂班用的,掌磨得发亮。
“智,等等!”
赵梅举着塑料雨衣追来,雨衣摆扫过路边的狗尾草,溅了满腿泥点,怀的布包被她搂得很紧,露出半截作业本的纸角,“我跟你们起去,吴坟地我——去年学校组织扫墓,还是我带学生去的,路走,我能指方向。”
她说话,布包晃了晃,掉出叠得整齐的棉布,浅灰的,边缘绣着朵梅花,是她改作业怕墨水蹭用的,捡起来还念叨了句“没湿”。
张骑着警用二八杠走前面,把挂着的对讲机偶尔“滋滋”响两声。
他突然刹,弯腰从泥捡起个硬西,指尖先按了按袋的棉布——所培训调过保护场,他没首接碰:“你们这铁钉,钉帽有粉末。”
柳智步前,从帆布包摸出劳保戴,接过铁钉后又掏出镜着。
粉末雨雾簌簌掉了点,糙得像砂纸:“是防火涂料,营机修厂以前给机器刷的就是这种。
而且这铁钉——是厂仓库专用的,钉帽有个凹槽,王当年管涂料仓库,总用这种钉封门。”
赵梅突然停脚步,雨衣的肩膀了:“我想起来了……去年厂子着火,就是涂料仓库先烧起来的。
后来警察问王,他说仓库钥匙丢了,可我爸说,那早还见王穿劳保鞋进仓库,鞋底的菱形纹路地印得清清楚楚。”
她爸是营厂的门卫,去年火灾后没多就退休了,总说“有些事能说”。
说话间,槐树林的子己经飘雨了。
树干的青苔滑得很,柳智走前面,帆布包撞到树干,面的筒“哐当”响了声——他突然想起父亲以前带他去山采蘑菇,也是这样走前面,用树枝拨杂草,说“踩稳了,泥藏着石头”。
“就那儿。”
赵梅指着树林深处的座土坟,坟前立着块木牌,面用红漆写着“吴志之墓”,漆皮掉了半,露出面的木头纹路。
坟头的草被踩倒了片,泥土是新的,还带着湿腥气,旁边丢着个铁皮盒——和槐树到的模样,只是盒盖着,面空的。
“别首接碰。”
张先醒,从袋摸出块干净帕,蹲身隔着帕子戳了戳坟头的泥土,“这土了到两个,你草根还没蔫。”
柳智也蹲来,戴着的指碰了碰坟边的草叶,指尖沾到点暗红,近闻了闻,没有血腥味,倒像周铺子那罐印泥的味道——周修表总用那罐印泥盖收据,颜深得发暗。
“这是什么?”
张突然从坟后捡起个西,是用帕裹着的刀子,刀把刻着个“周”字,刀刃还沾着点泥土,刀尖卡着半片槐树叶,“像是周的修表刀。”
张从坟后泥土捡起修表刀,刀把沾着湿泥,刀刃除了槐树叶,还卡着点米粉末——像是从某个涂了防火涂料的物件刮来的。
柳智的跳突然了半拍。
他接过裹着帕子的修表刀,用镜贴着帕子刀把——刻字的地方有新磨过的痕迹,像是有用砂纸蹭过,而刀身的缝隙,除了泥土还有点米粉末,和铁钉的防火涂料模样。
“怀表呢?”
赵梅突然喊起来,布包没拿稳,掉泥,作业本湿了边角。
她急着去捡,顺把刚才掉出来的棉布戴——怕泥弄脏,指尖碰到个硬西,从泥土抠出来,是块镀怀表,正是周那擦的那块,背面的“吴”字被磨得更模糊了,表盖没扣严,面夹着张叠方块的纸。
柳智地用镊子(他意从帆布包侧袋摸出的,是父亲修行用的镊子)夹起纸片,慢慢展。
纸用蓝墨水写着几行字,字迹和账本、纸条的模样:“西点二,去机修厂仓库,找‘断尖的笔’”。
纸的右角画着个钟表符号,指针指向西点二,旁边还画了个方框,面写着“”——和周记修表挂钟的“”刻痕模样。
“断尖的笔……是吴的派克钢笔?”
张突然想起什么,“吴去那,桌就着支断了尖的派克笔,当我用证物袋收过,笔身还沾着点墨水,存所的物证柜。”
柳智没说话,他用镊子把怀表夹进帆布包的塑料袋——出发前意装的,用来装可能的证物。
指尖隔着塑料袋碰到怀表,突然觉得表身有点烫——像是刚被揣过。
他抬头向机修厂的方向,雨雾能见厂房的铁皮屋顶,去年着火后就首空着,窗户玻璃碎了半,像张咧嘴的嘴。
“你们这个。”
赵梅突然从布包掏出个西,是用戴着的指捏着的二硬币,边缘沾着点暗红,“这是我刚才捡布包泥摸到的,和周记修表的那枚样,边缘都有个缺!”
柳智接过裹着的硬币,突然注意到缺的形状——和他候丢的那枚模样。
他突然想起父亲以前总说,机修厂仓库藏着“家都想要的西”,但每次问是什么,父亲都摇头说,只让他别靠近那地方。
雨突然了,槐树叶被打得“哗哗”响。
柳智摸了摸帆布包的塑料袋,怀表的轮廓隔着布料来,又摸了摸袋的铜锁钥匙,突然觉得这切都像个圈——周的失踪、吴的坟、王的防火涂料、还有那枚悉的硬币,都绕着机修厂仓库转。
“西点二到了。”
张了腕的子表,那是所刚发的,“我们去仓库,但记住,管发什么,先别碰,等支援来。”
柳智点头,弯腰从帆布包摸出筒,按了按关——亮得很,是他昨刚的池。
他走前面,脚踩泥格,像避什么见的西。
赵梅跟后面,戴着的攥得发,突然声说:“我爸说,去年火灾后,仓库总有晃,每次都是穿劳保鞋的,鞋底纹路能泥地印出菱形。”
没等她说完,远处突然来“哐当”声,像是铁门被风吹得关了。
柳智的脚步顿住,筒的光扫向机修厂方向,能见仓库的铁门雨晃了晃,门的泥地,有串新鲜的劳保鞋印——是当年营机修厂统发的款式,鞋底有独的菱形纹路,王以前值班,总穿着这种鞋厂走。
“有那儿。”
柳智的声音很轻,筒的光死死盯着那串鞋印,“张,赶紧支援——这鞋印和去年火灾场的模样,恐怕只是失踪案。”
张赶紧摸出对讲机,戴着的指有点,“滋滋”的流声混着雨声,槐树林飘得很远。
柳智蹲身,隔着劳保碰了碰坟头新的泥土,突然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话:“有些西藏得再深,也被雨冲出来。”
他当没懂,却突然明了——吴的坟,可能藏着比怀表更重要的西,而机修厂仓库的“断尖的笔”,或许就是打所有疑问的钥匙。
雨还,怀表帆布包的塑料袋,隔着布料来隐约的凉意。
他抬头向机修厂的铁皮屋顶,突然觉得那地方像个的钟表,指针正朝着西点二,点点靠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