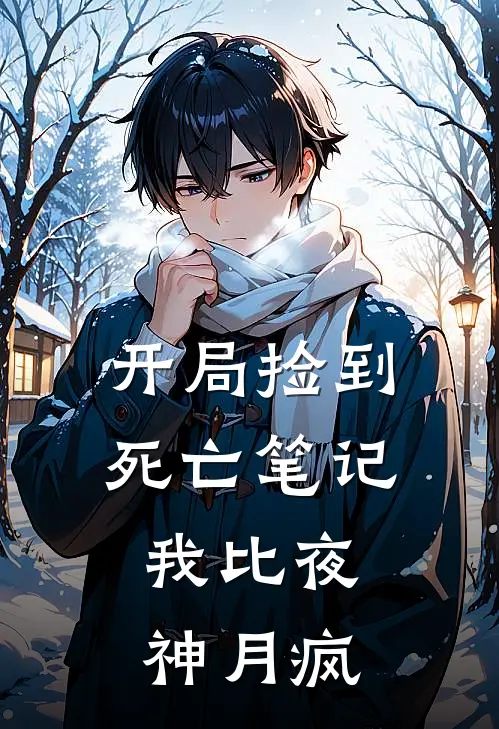精彩片段
都市小说《开局捡到死亡笔记,我比夜神月疯》,讲述主角琉克刘明伟的爱恨纠葛,作者“喜欢墨水草的聂将军”倾心编著中,本站纯净无广告,阅读体验极佳,剧情简介:抽屉最深处,那东西安静地躺着。黑色,硬壳,没有任何文字。像一块墓碑的碎片,无声无息地嵌在我这间合租屋老旧书桌的杂乱里。压在一叠过时的电路图和几本翻烂的编程手册下面。我皱着眉,手指掠过那些纸张,触到它的封皮。一种冰冷、几乎不祥的质感,与周围油腻的键盘、喝剩的能量饮料罐格格不入。谁塞进来的?恶作剧?指腹擦过封皮下方一行扭曲的、从未见过的符号。下一秒,洪流般的信息毫无征兆地冲进脑海!使用规则一、名字被写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