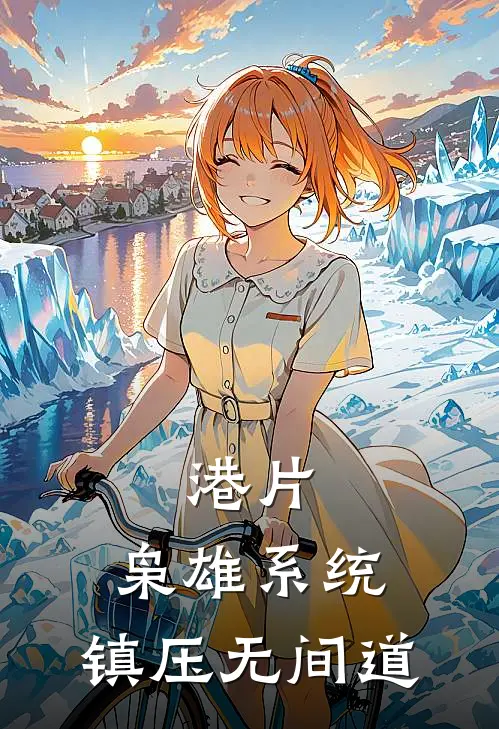精彩片段
都市小说《长风为旗我为天下守国门》,主角分别是张猛王勇,作者“樊晓林”创作的,纯净无弹窗版阅读体验极佳,剧情简介如下:大晟景和三年,暮春。汴梁的晨光总来得格外温柔,像被浸过温水的软绸,轻轻敷在这座皇城的每一寸角落。朱雀大街是汴梁的脊梁,从南城门一首延伸到皇宫外的承天门,青石板路被常年的车马碾得光滑如玉,昨夜刚下过一场小雨,此刻被晨光一照,竟泛着细碎的银光。街两侧的商铺早己开了门,酒肆的伙计正踮着脚,将写着“杏花村”的杏黄色幌子挂上门楣,木杆转动时,幌子上绣的酒坛图案轻轻晃动,仿佛能闻到坛里飘出的醇厚酒香;隔壁绸缎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