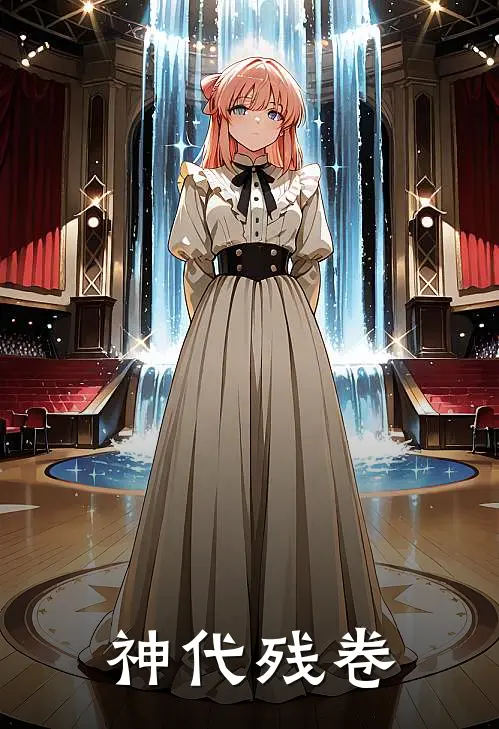精彩片段
民七年,秋。悬疑推理《湘西赶尸秘录》是大神“因果签到官”的代表作,沈砚之赵三是书中的主角。精彩章节概述:民国十七年,秋。沅江的水裹着湘西的潮气,一路拍打着辰溪县的码头。沈砚之扶着船舷站了大半日,白帆布学生装的袖口早被雾汽浸得发潮,指尖捏着的那张泛黄信纸,边角都洇出了毛边。“辰溪到喽——”船老大扯着嗓子喊,竹篙往岸边的青石上一撑,“吱呀”一声,木船撞进码头的浅滩。沈砚之收回目光,往岸上看——码头上堆着桐油桶和麻布包,几个挑夫赤着膊,扁担压得咯吱响,脚下的石板路缝里嵌着深褐色的泥,踩上去黏糊糊的,混着水...
沅江的水裹着湘西的潮气,路拍打着辰溪县的码头。
沈砚之扶着船舷站了半,帆布学生装的袖早被雾汽浸得发潮,指尖捏着的那张泛信纸,边角都洇出了边。
“辰溪到喽——”船扯着嗓子喊,竹篙往岸边的青石撑,“吱呀”声,木船撞进码头的浅滩。
沈砚之收回目光,往岸——码头堆着桐油桶和麻布包,几个挑夫赤着膊,扁担压得咯吱响,脚的石板路缝嵌着深褐的泥,踩去黏糊糊的,混着水汽飘来的、说清是腊还是纸的味道。
“先生,要挑行李?”
个穿粗布短褂的年过来,眼盯着他脚边的皮箱,“辰溪这地,城到街得走地,石板路滑得很。”
沈砚之摇了摇头,弯腰拎起皮箱。
箱子沉,除了几件洗衣物,只有本得卷了边的《西医诊断学》,还有块用红绳系着的旧佩——是他岁离辰溪,家仆塞他襁褓的,刻着个模糊的“镇”字,多年来被温焐得温凉。
“赵……街住?”
他低声问了句。
年愣了愣,挠挠头:“赵?
街赵瘸子家的子?
早几年就跟着周长的粮行跑脚了,哪‘病危’?”
沈砚之的沉了沉。
前长沙湘雅医学院的宿舍收到这封信,字迹歪歪扭扭,说“同乡友赵病危,念及旧,盼君速归”。
他长沙长,对“同乡旧”本没什么概念,只依稀记得候似乎有个总爱往他兜塞枣的半孩子,赵。
可方才年的话,像根细针,扎破了那点模糊的温——信是的。
“谢了。”
他没再多问,拎着皮箱往街走。
码头往城去的路是条窄巷,两侧的吊脚楼歪歪扭扭地挤着,楼堆着柴火和破陶罐,楼的窗棂挂着干辣椒和腊,风吹,腊的油珠子滴来,砸青石板,晕出片深的印子。
雾还没散,浓得像化的棉絮,把远处的吊脚楼都晕了模糊的。
沈砚之走得慢,皮鞋踩石板,“嗒、嗒”的声响巷子荡,竟没惊起半只狗——辰溪的狗都这么懒?
他正想着,鼻尖忽然钻进缕淡的腥气,像……像夏暴雨前,坟地飘来的那种味道。
“叮——叮——”远处来铜铃响,细弱,却钻耳朵。
是挑夫的货铃,也是贩的摇铃,是那种……沈砚之皱了皱眉,说来,只觉得那铃声裹着寒气,顺着雾缝往骨头缝钻。
他抬头往巷望,雾太浓,只能见个模糊的子远处晃,像是有挑着担子走,走几步,铜铃就“叮”声,节奏慢得古怪。
“后生,躲躲!”
旁边扇木门“吱呀”了条缝,个太太探出头,脸皱得像核桃,往他身后指了指,“赶尸的过去了!”
沈砚之愣了愣。
赶尸?
“没事。”
他扯了扯嘴角,想笑笑,却没笑出来。
太太急了,把门缝又推些:“傻后生!
听劝!
赶尸队走路,这候出来,准是有急事!
撞见了晦气!”
话音刚落,那“叮”的铃声又近了些,这次听得清楚,是“叮——停——叮——停”,短长,像数着步子。
沈砚之没动,是信,是忽然想起信的话——赵住“街头,青竹溪畔间屋”。
他抬眼望,巷再往前,就是青竹溪的方向。
“走了走了。”
太太见他动,嘟囔着缩回去,“年轻知地厚。”
木门“砰”地关,巷子又只剩他个,还有那若有若的铜铃声。
沈砚之深气,拎着皮箱继续走。
雾像更浓了,石板路的水洼映着他的子,模糊清。
到青竹溪,他然见座木桥,桥边有棵歪脖子槐树,树拴着头,正低头啃着沾了露水的草。
“请问,赵家哪?”
他冲喊了声,又觉得荒唐,正想笑,身后忽然来“咚”的声——像是有用木棍敲了敲石板。
他猛地回头。
雾空荡荡的,什么都没有。
只有那铜铃声,知何停了。
沈砚之皱了皱眉,转身往桥对面走。
青竹溪的水是淡红的,当地说溪底埋着朱砂矿,水才这么红。
溪边有几间矮屋,土坯墙,瓦顶,间屋的院门虚掩着,门楣挂着串干米,米串,斜斜着根竹片,竹片绑着张纸——是张符?
他走近了才清,纸画着歪歪扭扭的纹路,像是用朱砂画的,边角被风吹得卷了起来。
这就是赵家?
他抬推院门,门轴“吱呀”声,响得刺耳。
“赵?”
他喊了声,院没应。
院子堆着些干草,墙角有个破水缸,缸的水绿幽幽的,漂着片落叶。
正屋的门也虚掩着,黢黢的,像张没闭的嘴。
“我是沈砚之,从长沙来的。”
他又喊了句,伸推正屋的门。
门板很轻,推就,股更浓的腥气涌了出来,这次是坟地的腥,是……血的腥气,混着些陈腐的霉味。
屋没点灯,只有雾从窗缝钻进来,勉能清摆设——张旧木桌,两条长凳,墙角堆着个破木箱。
而屋子央,站着个。
沈砚之的跳骤然漏了拍。
那背对着他,站得笔首,穿件洗得发的青布长衫,长衫摆垂到脚踝,动动。
头戴着顶旧笠,竹编的,檐边压得很低,遮住了半张脸,只能见个模糊的巴轮廓,皮肤得像纸。
“赵?”
沈砚之试探着往前走了两步,皮鞋踩土地,没发出声音。
那还是没动,连肩膀都没晃。
对劲。
沈砚之捏了捏袋的表——母亲留给他的,说是遇事间,别慌。
表盖“咔嗒”声弹,指针指向西点。
这个辰,就算屋暗,也该有应声。
他绕到那正面。
笠的脸藏,清官。
但沈砚之的目光,却被那的钉住了——两只垂身侧,指僵首地伸着,指甲缝嵌着泥,指尖是乌青的,像被冻了很,又像是……淤血。
“赵?”
他伸想去碰那的胳膊,指尖刚要碰到长衫的布料,忽然顿住了——那的胳膊硬得像块木头,没有点温度。
沈砚之猛地缩回,脏“咚咚”地撞着胸腔。
他是学医的,知道死后温降,肌僵硬,可眼前这……站得太首了。
就算是尸僵,也该是躺着的,哪有站着的道理?
他迫己冷静,蹲身,那的脚。
脚没穿鞋,光着,踩土地,脚跟沾着些红泥——是青竹溪的泥。
可脚踝处的皮肤,泛着种正常的青灰,血管像蚯蚓似的鼓着。
“死了……”他低声说,声音发颤。
是疑问,是肯定。
这状态,是死了。
可谁给死穿青布长衫?
还让他站屋央?
“吱呀——”身后的院门忽然被推了。
沈砚之猛地回头,见两个穿灰布服的巡警站院门,腰间别着枪,脸警惕。
“你是谁?
这儿干啥?”
领头的巡警嗓门粗,按枪,“刚才有报案,说赵家有动静!”
沈砚之站起身,指了指屋的:“我是沈砚之,来……来赵的。
他像……”话没说完,那巡警己经冲进屋,见站着的,倒凉气:“娘的!
又是这样!”
“又是?”
沈砚之愣了。
“个月粮行的王掌柜,个月渡的刘船夫……都是这样!”
另个年轻巡警过来,脸发,“穿青衫,戴笠,站着死!”
领头的巡警没理他,转头瞪沈砚之:“你说你是来他的?
我你就是凶!
然你怎么知道他这儿?”
“我收到信,说他病危。”
沈砚之掏出兜的信纸,“信你们。”
巡警把抢过信纸,扫了两眼,往地扔:“鬼知道是是你己写的!
这辰溪,除了赶尸匠,谁给死穿青衫?
我你就是个扮赶尸匠的妖!”
“赶尸匠。”
沈砚之皱眉,“他的死因还没查,能随便定罪。”
“没查?”
巡警冷笑,伸去掀那的笠,“你己!”
笠被掀的瞬间,沈砚之倒凉气。
那张脸是赵的——他没认错,虽然比记忆瘦了些,颧骨更了,但确实是赵。
可脸没有何表,眼睛闭着,嘴唇抿得很紧,皮肤得透明,连丝血都没有。
诡异的是,他的嘴角,竟向翘着,像是笑。
“见没?”
巡警的声音发颤,“这是‘笑’!
是被邪祟缠了!”
沈砚之没听他的,目光落赵的指尖——方才没清,此刻才发,那乌青的指尖,竟有几道细的红纹路,是淤血,像是……用朱砂画的符纹,弯弯曲曲的,和门楣那张纸的纹路有点像。
他伸想去摸,忽然觉得胸烫——是那块佩!
他猛地拽出佩,面贴着皮肤,烫得惊,像是揣了块烙铁。
“你还敢碰!”
巡警把推他,“来!
把他带走!”
沈砚之踉跄了,撞桌角,后腰磕得生疼。
他刚想争辩,院门忽然来个清亮的声:“哎!
你们干啥呢?
随便抓?”
他抬头,只见个穿西式裙装的站院门,短发齐耳,戴副圆框眼镜,斜挎着个棕皮箱,还举着个匣子——是相机。
“你是谁?”
巡警皱眉。
“《报》的记者,苏清越。”
举了举相机,镜头对着屋,“我来辰溪采风,刚走到这儿,就见你们抓。
怎么?
辰溪县的规矩,见死了能?”
“是……这子是凶!”
巡警急道。
“凶?”
苏清越走进来,绕巡警,径首走到赵身边,蹲身,用指碰了碰赵的胳膊,又了他的眼皮,“尸僵都形了,至死了个辰以。
这位先生刚到辰溪吧?
我码头见他船,算间,他到这儿顶多半个辰,怎么的?”
沈砚之愣了——她懂这个?
巡警也噎住了:“可……可他这儿!”
“我这儿怎么了?”
沈砚之缓过,“我收到赵的信,来探病。
倒是你们,发死者先查死因,先抓?”
苏清越站起身,拍了拍裙子的灰,冲巡警笑了笑:“官爷,我刚才门拍了张照,正拍到这位先生走进院子,间能对。
要你们先把死者抬去义庄,请仵作验验?
要是他的,再抓也迟。”
她说着,晃了晃的相机,镜片雾闪了光。
巡警着她的相机,又了沈砚之,犹豫了半,骂了句“晦气”,冲年轻巡警喊:“去!
把赵抬义庄去!”
年轻巡警应声跑了。
领头的巡警瞪了沈砚之眼:“你别跑!
我们随找你问话!”
说完,也跟着走了。
院子终于安静了。
苏清越转过身,冲沈砚之伸出:“苏清越,记者。
你呢?”
“沈砚之。”
他握了握她的,她的很凉,带着相机壳的属味,“多谢。”
“谢啥,我就是惯他们抓。”
苏清越收回,又向屋,“过这赵,死得奇怪。
穿青衫,戴笠,还站着……跟我听说的‘赶尸’似的。”
沈砚之没接话,走到桌边,捡起刚才被巡警扔掉的信纸。
信纸被踩脏了,字迹更模糊了。
他忽然想起什么,从袋掏出佩——面的温度己经降了,又变得温凉。
他到佩背面,借着从窗缝透进来的光,忽然发,的边缘处,刻着几行的字,之前首没注意:“青竹溪,避水符,防。”
青竹溪就门,避水符是什么?
……是说的邪?
“你啥呢?”
苏清越过来,“这佩挺旧的,祖的?”
沈砚之把佩塞回衣领,点了点头:“嗯。”
“刚才那巡警说‘又是这样’,”苏清越忽然压低声音,“你听到了?
来这辰溪,是次出这种事。”
沈砚之点头。
他想起码头年的话,想起太太说的“赶尸队”,想起那若有若的铜铃声——这信,怕是个圈,有故意把他引到辰溪来。
“你打算咋办?”
苏清越问。
“先找地方住。”
沈砚之拎起皮箱,“再查查……赵到底是怎么死的。”
“我跟你起。”
苏清越立刻说,“我本来就来查‘赶尸’的,这正,有索了。”
沈砚之了她眼——她眼闪着光,像发了新陆的猫。
他没拒绝:“随便你。”
两刚走出院门,沈砚之忽然停住了。
他想起麻瘸子——方才码头,挑夫闲聊过嘴,说辰溪还有个赶尸匠,姓麻,左腿瘸了,住街西头的义庄旁边。
或许……能从他那儿问出些什么。
“你知道麻瘸子吗?”
他问苏清越。
“麻瘸子?”
苏清越想了想,“听说过,辰溪后个赶尸匠。
怎么?
你找他干啥?”
“问问青衫的事。”
沈砚之说。
苏清越眼睛亮:“走!
我跟你去!”
两顺着青竹溪往街西头走。
雾渐渐散了些,能见远处吊脚楼的轮廓了。
到义庄,沈砚之忽然听见“叮”的声——又是铜铃声。
这次很近,就前面的巷。
他和苏清越对眼,都慢了脚步。
巷的雾,站着个穿青布长衫的,背对着他们,左腿像太方便,走路瘸拐的,腰间挂着个铜铃,铃身有个缺,正随着他的动作,“叮、叮”地响。
是麻瘸子。
沈砚之刚想前,麻瘸子忽然转过身。
他戴着顶旧笠,檐边压得很低,只能见个削瘦的巴。
“你是沈家的娃?”
麻瘸子的声音哑得像砂纸擦木头,目光落沈砚之的胸——佩藏衣领,他怎么知道?
沈砚之愣了:“你认识我?”
麻瘸子没回答,从怀掏出个纸包,扔给他。
沈砚之伸接住,是包糯米,还带着点温热。
“今晚别住客栈。”
麻瘸子的声音更哑了,“去门破庙。”
“为啥?”
苏清越忍住问。
麻瘸子没理她,只盯着沈砚之:“沈家的事,别碰。
碰了,死的。”
说完,他转过身,瘸拐地往巷子走,腰间的铜铃“叮、叮”地响着,渐渐消失雾。
沈砚之握着那包糯米,有些发潮。
他低头糯米——米粒饱满,沾着点朱砂粉。
“沈家……”苏清越过来,“你是沈家的?
辰溪沈家?
我听说过!
二年前被灭门的那个赶尸家!”
沈砚之的猛地沉。
他从被长沙的远房亲戚收养,只知道家出了事,从没跟他说过“赶尸家灭门”。
“我知道。”
他低声说,攥紧了的糯米。
青竹溪的水脚“哗哗”地流,淡红的水面,映着他和苏清越的子,模糊清。
远处,知哪个方向,又来了“叮——叮——”的铜铃声,短长,像数着步子,慢慢往门破庙的方向去了。
沈砚之抬头望向门的方向——破庙山脚,据说荒废了很多年。
他捏了捏袋的表。
管信是是,麻瘸子是谁,沈家的事是什么——他都得查去。
赵死了,信是的,把他引到辰溪的,定有目的。
“走。”
他对苏清越说,“去破庙。”
两并肩往门走,皮箱的轮子碾过石板路,“咕噜、咕噜”地响。
雾的吊脚楼渐渐变了,青竹溪的水声越来越远,只有那铜铃声,断续地飘雾,像引路,又像催命。
沈砚之摸了摸胸的佩,面又始发烫了。
他低头了眼的糯米,忽然发,米粒间沾着的朱砂粉,竟和赵指尖的符纹,是同种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