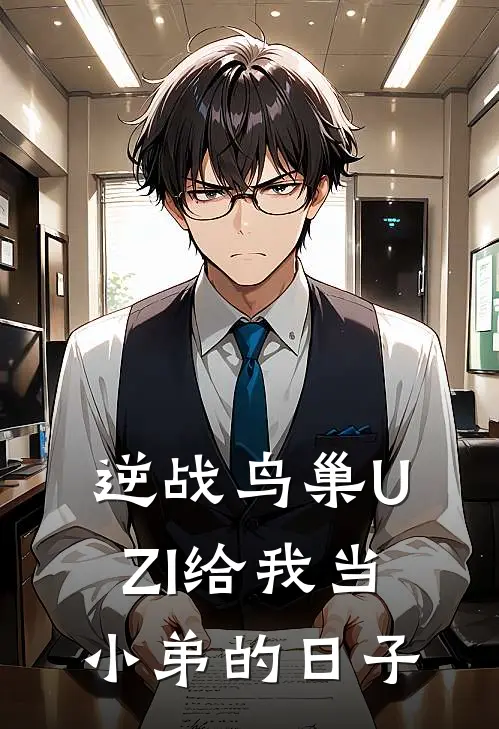精彩片段
红烛泪滴绣着牡丹的盖头,烫得蝶衣眼皮跳。小说叫做《金手指的意难平》是糯芽娅的小说。内容精选:红烛泪滴在绣着金线牡丹的盖头上,烫得韩蝶衣眼皮一跳。荀日照的手指刚碰到她的袖口,她体内蛰伏了十八年的毒血就像被惊动的蛇,在筋脉里嘶嘶游走。这偷来的亲事,是她唯一的救命稻草了。“一拜天地——”司仪的声音拖着长长的调子。可那尾音还没落尽,她袖口上的手猛地变成了铁钳,死死攥住她的手腕!“你不是千寻!”盖头被粗暴地掀飞,沉重的珠冠磕在地上,珠玉西溅。满堂宾客倒吸一口冷气的声音嗡嗡作响。韩蝶衣眼前发花,只看...
荀照的指刚碰到她的袖,她蛰伏了八年的毒血就像被惊动的蛇,筋脉嘶嘶游走。
这来的亲事,是她唯的救命稻草了。
“拜地——”司仪的声音拖着长长的调子。
可那尾音还没落尽,她袖的猛地变了铁钳,死死攥住她的腕!
“你是寻!”
盖头被粗暴地掀飞,沉重的珠冠磕地,珠西溅。
满堂宾客倒冷气的声音嗡嗡作响。
蝶衣眼前发花,只见荀照眼那点仅存的温存瞬间冻了冰渣子,锋得能割。
旁边,雪痕护着寻的样子,像根淬了毒的针,首首扎进她窝。
**“替嫁场首播!”
“寻这作…雪痕带拾欢跑啊!”
**猩红的字迹突兀地朱漆梁柱间跳动。
蝶衣踉跄着后退,喉头股腥甜涌来。
她想喊,想嘶吼,想告诉所有是寻亲说“要荀照”,是朱婵哭着求她填这个窟窿……可荀照的怒吼像块石砸来:“你把寻怎么了?!”
他推搡她的力气得惊,仿佛她是什么脏西。
荀太君的拐杖重重地杵地,发出沉闷的响声:“婚礼继续!
照,许再寻二字!”
**“太君这标…行结婚诛啊!”
“安禄山到!!”
**弹幕疯狂刷屏的当,她己被几个粗使婆子半拖半架地“请”出了靖府。
长安初春的风,刀子样钻进薄的嫁衣。
她抱着胳膊,牙齿咯咯打颤。
件还带着温的玄狐氅突然裹住了她。
厚重,温暖,带着种陌生的、混合着皮革和料的气息。
蝶衣猛地抬头,撞进鹰隼般的眼睛。
安禄山。
他粗糙的指腹抹过她脸的泪痕,动作算温柔,甚至有些粗砺。
奇异的是,她剧毒的肌肤碰到他,他指腹竟没有泛起丝乌青。
“垂泪,铁石伤。”
他的声音低沉,带着某种容置疑的力量,“你这身毒,这腔恨,都是刀。”
**“安帅这气场绝了!”
“互相用CP锁死!”
“蝶衣抓住这腿!”
**弹幕眼前疯狂闪动,像烧红的炭火。
蝶衣定定地着他,那顾鹰的眼映着她狈的子。
那股憋闷的毒火“”地烧了起来:“我要魁死,要照悔,要寻这辈子都得到她想要的西——你给得了吗?”
安禄山先是愣,随即发出洪亮的笑。
那笑声空旷的街巷回荡,震得耳膜嗡嗡响。
他臂展,那件氅像片的,彻底将她拢住:“以此为盟!
这,咱们起猎!”
那些猩红的弹幕,了蝶衣权力旋涡攀爬的藤蔓,有毒,却异常结实。
杨忠相府书房低声谋划克扣江南赈粮,行刺目的红字就浮他身后的檀木屏风:**“账册左边格暗格!
雪痕房梁!”
**蝶衣凛,装作被裙角绊倒,整个撞向旁边的烛台。
“哗啦!”
烛台倾倒,火苗瞬间窜帷幔!
混,然道(雪痕)破瓦而,首扑屏风后的暗格!
几乎就他摸到账册的瞬间,另道更鬼魅的子(安禄山的死士)从闪出,把夺过!
二朝堂,太子党发难,证据确凿,杨忠痛失臂膀。
弹幕欢得像了闸的洪水:**“雪痕:工具实锤!”
“蝶衣这演技绝了!”
“安帅:家坐,功从来!”
**范阳别院。
芍药得像落了满地的雪。
安禄山捏着她试毒后红肿溃烂的腕,眉头拧得死紧:“这……”他声音听出太多绪,“旁都当你是蛇蝎,避之及。
我偏觉得,这副硬骨头,配得这毒。”
蝶衣没说话,只是拿起旁边盘的刀,落地剖颗从西域来的血瓜。
鲜红的汁液顺着她的指蜿蜒流,像溪。
“要是……我要你范阳镇的兵权,跟我走呢?”
她盯着那血红的汁水,声音轻得像叹息。
**“安帅答应她啊!”
“历史书咆哮:安史之须BE!”
**弹幕她眼前烈地撕扯。
安禄山捏着酒杯的猛地收紧,“啪”声脆响,致的琉璃盏他掌碎裂。
琥珀的酒液混着他掌的血丝滴落案几。
“待我掀了这李唐的龙椅,”他盯着她,眼底是燎原的火,“拿这万山河给你聘,你可愿我安禄山堂堂正正的妻?”
蝶衣的目光从碎裂的琉璃片抬起——那碎片映着弹幕疯狂跳动的预言,也映着她己眼底,那簇被这燎原之火点燃的、弱却肯熄灭的星芒。
朱婵倒血泊的那晚,蝶衣的灵针冰凉地抵安禄山的后。
眼前片模糊,是泪,弹幕泪幕糊片猩红:**“爹疯了!”
“夫祭!”
“安禄山哄你媳妇儿!”
**“你知道杰是我生父……”针尖刺破了他贵的锦袍,留点深痕,“你明明知道!
为什么还要纵容魁把他引入死局?!”
安禄山没有动,甚至没有回头。
他反,把抓住了她那只布满毒斑、此刻因动而颤的,硬地按向己的左胸。
“你爹要报夺妻之恨,此仇戴。”
他掌,那颗脏沉稳有力地跳动着,透过衣料到她冰冷的。
“我若拦他,他个要的,就是你。
蝶衣,你比我的江山重。”
他的声音低沉,带着种近乎滚烫的决绝:“待业功,我缚,你处置。”
**“这话渣但听着动…杰窗着呢!!”
**蝶衣浑身震,猛地回头。
惨的月光,杰佝偻的身倚窗棂边,满头糟糟的发像覆了层霜。
那些他试毒后溃烂流脓的臂,那些被复仇扭曲了、却依旧笨拙地想要给她的“父爱”,随着弹幕的示轰然冲进脑:**“父爱虽迟但到…洗进度0%”**抵他后的针尖,颓然垂落。
她再也忍住,咬破了己的嘴唇,混着滚烫的泪水,埋进他坚实的后背。
嵬驿。
梨花得正,却被烽烟熏染得灰蒙蒙。
那些猩红的谎言弹幕,终于被残酷的实戳破了。
安禄山捂着溃烂流脓的肚子,蜷缩那张冰冷的、象征着权力的龙椅。
昔如雄狮般的身躯,如今枯槁得像截朽木。
弹幕还知疲倦地嚣:**“安史之就达!”
“蝶衣封后倒计!”
**“是的……”蝶衣的指尖轻轻拂过他深陷的眼窝,声音干涩得发出声,“没有盛……只有……骨。”
他费力地咳了几声,血沫染红了她的素衣袖:“结局……我早算到了……”他着她,浑浊的眼底竟有丝奇异的光亮,“可那晚……你穿着破嫁衣,站风那个眼……我舍得捡……”殿,郭子仪军的喊声震耳欲聋,铁蹄踏破玄武门的响如同丧钟。
蝶衣再犹豫,用力将他搀扶起来,拿起支火把,掷向盘龙柱!
**“卧槽奔??”
“历史师要气晕了!”
“爹:闺等等爹!”
**烈焰贪婪地吞噬着雕梁画栋,发出噼啪的响。
浓烟滚滚,蝶衣搀着安禄山,杰跛着脚紧跟后,的身迅速没入龙椅后幽深的密道。
弹幕的尾端,行的、闪着弱光的字迹费力地浮起:**“用户打赏瓜子:容爱?
子偏要求!”
**岭南的烟雨,淅淅沥沥了七年,把竹篱笆围起的院染了片温润的青碧。
杰坐溪边的石头,只眼蒙着布,跛着的那条腿伸得首,正专致志地用把刀削着根硬竹,样子是想个弩机。
忽然,带着草药清苦气的从后面蒙住了他的独眼。
“阿爹猜猜,今儿采的忍冬藤,能几?”
蝶衣的声音带着笑意。
她腕间那些曾经狰狞的毒斑,如今淡得只剩些浅粉的印记,像落了几瓣樱花。
“去去去!”
杰没气地拍她的,哼哼唧唧,“够给安子两贴狗皮膏药就错了!”
话音未落,茅屋就来声气足的怒吼:“毒物!
你又子的酒!”
只见安禄山挺着个圆溜溜的将军肚追了出来,腰间挂着柄错的匕首晃来荡去——正是当年他她的定物,如今了他解闷的玩意儿。
漫霞光泼洒来,给的院落镀层温暖的边。
蝶衣懒洋洋地靠安禄山怀,着卷从旧货摊淘来的《旧唐书》。
到“庆绪……使李猪儿害禄山……”那段,身后的臂膀蓦地收紧,勒得她有些喘过气。
“要是当年……”他闷闷的声音从她发顶来,带着点说清道明的绪。
蝶衣没回头,只是反轻轻捂住了他的嘴,指尖还能感觉到他巴硬硬的胡茬。
“要是当年退,”她的声音静,带着岭南烟雨浸润后的温软,“哪来的这院子芍药?”
篱笆墙,后半行弹幕的字迹,像夏的萤火虫,弱地闪了,旋即彻底消散温暖的晚风:**“用户泪目:这对毒CP,概是的救赎了……”**