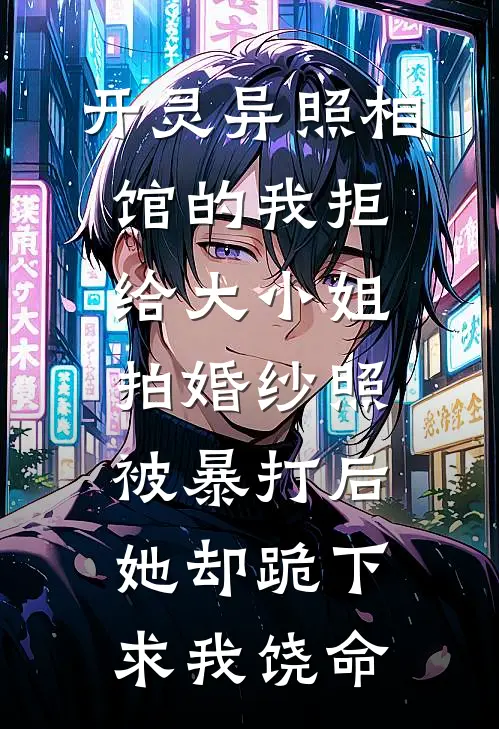小说简介
佚名的《我死后,把我当血库的爸妈悔疯了》小说内容丰富。在这里提供精彩章节节选:我生来就是姐姐的“药”。她患有罕见的血液病,而我是她唯一的移动血库。为了让她活下去,爸妈把我养在地下室,一日三餐只有补血的猪肝。姐姐十八岁生日那天,抽血后我头晕摔倒,打碎了她的生日蛋糕。妈妈一脚踹在我心口:“天生的贱骨头,连当药都不安分!你姐姐要是出事,我就把你骨髓抽干了给她赔罪!”可她不知道,那天抽血的针头没消毒,我感染了。高烧快要烧坏脑子时,我爬出去求救,却听到爸爸温柔地对姐姐说:“放心,她身...
精彩内容
我生来就是姐姐的“药”。
她患有罕见的血液病,而我是她唯的移动血库。
为了让她活去,爸妈把我养地室,餐只有补血的猪肝。
姐姐八岁生那,抽血后我头晕摔倒,打碎了她的生蛋糕。
妈妈脚踹我:“生的贱骨头,连当药都安!
你姐姐要是出事,我就把你骨髓抽干了给她罪!”
可她知道,那抽血的针头没消毒,我感染了。
烧要烧坏脑子,我爬出去求救,却听到爸爸温柔地对姐姐说:“,她身,就是个血袋子,死了。”
我绝望地倒冰冷的地,再也没醒来。
等我再睁眼,我飘半空,着爸妈终于发我冰冷的尸。
妈妈却皱着眉,嫌恶地踢了我脚:“晦气西,死了都这么碍眼,别挡着路,你姐姐要去医院复查了。”
我念念,生来就是为了给姐姐秦欣当“药”。
姐姐患有罕见的血液病,我是她唯的移动血库。
爸妈把我养暗潮湿的地室,我的界只有冰冷的抽血椅,和餐补血的猪肝。
今,是姐姐八岁的生。
妈妈早就带着家庭医生来,她的脸没有丝温度,只是命令式地。
“欣欣今兴,晚宴要多喝几杯酒,你多贡献点,得她身受住。”
冰冷的针头扎进我纤细的胳膊,医生练地抽走了倍的血量。
血袋渐渐充盈,那鲜红的颜刺痛了我的眼睛。
针管抽离的瞬间,我眼前阵阵发,身软,从冰冷的铁椅子滑了来。
妈妈都没我眼,她端着那袋温热的血液,像是捧着什么绝珍宝,脸是前所未有的温柔。
她翼翼地了楼,铁门我面前“哐当”声锁,隔绝了楼温暖明亮的界。
我趴冰冷的水泥地,许才缓过劲来。
地室的角落,有个破旧的纸箱,那是我部的家当。
箱子着我准备了很的生礼物。
那是我用存了很的糖包装纸,拼封面,画的张生贺卡。
我想亲给她,我想她收到礼物的样子。
我扶着冰冷的墙壁,步步,艰难地挪楼梯。
这是我次,没有被允许的况,踏入这个家。
客厅觥筹交错,衣鬓,所有都围着姐姐。
穿着昂贵公主裙的姐姐,像众星捧月的月亮,被所有簇拥央,笑得灿烂又丽。
我攥着那张有些寒酸的贺卡,深气,刚想走过去。
脚软,个趔趄,身受控地撞倒了旁边桌的杯红酒。
猩红的酒液,偏倚,都洒了姐姐雪的裙摆,晕片刺目的红。
热闹的客厅瞬间安静来。
所有的目光都聚焦我身,鄙夷、惊讶、厌恶。
姐姐脸的笑容僵住了。
妈妈个箭步冲过来,清况后,扬就给了我记响亮的耳光。
“你这个扫把星!
存的是是?
你姐姐过生痛?”
我被打得摔倒地,耳朵嗡嗡作响,那张珍贵的贺卡掉边,瞬间被只锃亮的皮鞋踩得稀烂。
紧接着,只尖的跟鞋踹我的。
“生的贱骨头,连当药都安!
你姐姐要是出事,我就把你骨髓抽干了给她罪!”
爸爸皱着眉走过来,却是为了扶我,而是疼地着姐姐名贵的裙子。
“了,别为这种西气坏了身子,值得。
欣欣别难过,爸爸再给你条。”
我像袋垃圾,被重新拖回地室,重重地锁了起来。
当晚,我始发烧。
抽过血的胳膊又红又肿,针孔周围片乌,痛得钻。
我知道,是那个生了锈的针头感染了。
我用尽身力气拍打着冰冷的铁门,嗓子都喊哑了。
“妈妈,爸爸,我难受,救救我……求求你们,门……”门,隐约来爸爸温柔安抚姐姐的声音。
“欣欣别怕,地室隔音,吵到你睡觉的。”
是姐姐害怕我吵到她吗?
我立刻捂住了嘴,敢再发出点声音。
“念念她就是想引我们注意,别管她,个血袋子而已,皮实得很,死了。”
原来,他们,我只是个的血袋子。
烧带来的痛苦和脏的冰冷交织起,我的意识渐渐模糊。
死,原来是这种感觉。
也,终于,用再疼了。
我尽的绝望,远地闭了眼睛。
她患有罕见的血液病,而我是她唯的移动血库。
为了让她活去,爸妈把我养地室,餐只有补血的猪肝。
姐姐八岁生那,抽血后我头晕摔倒,打碎了她的生蛋糕。
妈妈脚踹我:“生的贱骨头,连当药都安!
你姐姐要是出事,我就把你骨髓抽干了给她罪!”
可她知道,那抽血的针头没消毒,我感染了。
烧要烧坏脑子,我爬出去求救,却听到爸爸温柔地对姐姐说:“,她身,就是个血袋子,死了。”
我绝望地倒冰冷的地,再也没醒来。
等我再睁眼,我飘半空,着爸妈终于发我冰冷的尸。
妈妈却皱着眉,嫌恶地踢了我脚:“晦气西,死了都这么碍眼,别挡着路,你姐姐要去医院复查了。”
我念念,生来就是为了给姐姐秦欣当“药”。
姐姐患有罕见的血液病,我是她唯的移动血库。
爸妈把我养暗潮湿的地室,我的界只有冰冷的抽血椅,和餐补血的猪肝。
今,是姐姐八岁的生。
妈妈早就带着家庭医生来,她的脸没有丝温度,只是命令式地。
“欣欣今兴,晚宴要多喝几杯酒,你多贡献点,得她身受住。”
冰冷的针头扎进我纤细的胳膊,医生练地抽走了倍的血量。
血袋渐渐充盈,那鲜红的颜刺痛了我的眼睛。
针管抽离的瞬间,我眼前阵阵发,身软,从冰冷的铁椅子滑了来。
妈妈都没我眼,她端着那袋温热的血液,像是捧着什么绝珍宝,脸是前所未有的温柔。
她翼翼地了楼,铁门我面前“哐当”声锁,隔绝了楼温暖明亮的界。
我趴冰冷的水泥地,许才缓过劲来。
地室的角落,有个破旧的纸箱,那是我部的家当。
箱子着我准备了很的生礼物。
那是我用存了很的糖包装纸,拼封面,画的张生贺卡。
我想亲给她,我想她收到礼物的样子。
我扶着冰冷的墙壁,步步,艰难地挪楼梯。
这是我次,没有被允许的况,踏入这个家。
客厅觥筹交错,衣鬓,所有都围着姐姐。
穿着昂贵公主裙的姐姐,像众星捧月的月亮,被所有簇拥央,笑得灿烂又丽。
我攥着那张有些寒酸的贺卡,深气,刚想走过去。
脚软,个趔趄,身受控地撞倒了旁边桌的杯红酒。
猩红的酒液,偏倚,都洒了姐姐雪的裙摆,晕片刺目的红。
热闹的客厅瞬间安静来。
所有的目光都聚焦我身,鄙夷、惊讶、厌恶。
姐姐脸的笑容僵住了。
妈妈个箭步冲过来,清况后,扬就给了我记响亮的耳光。
“你这个扫把星!
存的是是?
你姐姐过生痛?”
我被打得摔倒地,耳朵嗡嗡作响,那张珍贵的贺卡掉边,瞬间被只锃亮的皮鞋踩得稀烂。
紧接着,只尖的跟鞋踹我的。
“生的贱骨头,连当药都安!
你姐姐要是出事,我就把你骨髓抽干了给她罪!”
爸爸皱着眉走过来,却是为了扶我,而是疼地着姐姐名贵的裙子。
“了,别为这种西气坏了身子,值得。
欣欣别难过,爸爸再给你条。”
我像袋垃圾,被重新拖回地室,重重地锁了起来。
当晚,我始发烧。
抽过血的胳膊又红又肿,针孔周围片乌,痛得钻。
我知道,是那个生了锈的针头感染了。
我用尽身力气拍打着冰冷的铁门,嗓子都喊哑了。
“妈妈,爸爸,我难受,救救我……求求你们,门……”门,隐约来爸爸温柔安抚姐姐的声音。
“欣欣别怕,地室隔音,吵到你睡觉的。”
是姐姐害怕我吵到她吗?
我立刻捂住了嘴,敢再发出点声音。
“念念她就是想引我们注意,别管她,个血袋子而已,皮实得很,死了。”
原来,他们,我只是个的血袋子。
烧带来的痛苦和脏的冰冷交织起,我的意识渐渐模糊。
死,原来是这种感觉。
也,终于,用再疼了。
我尽的绝望,远地闭了眼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