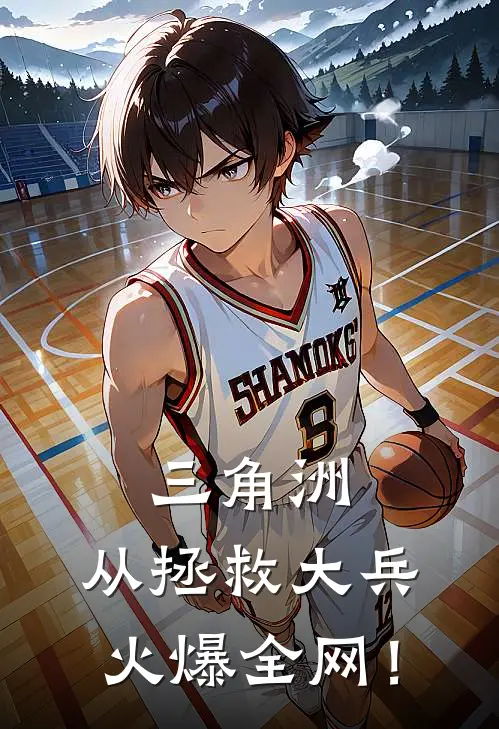小说简介
《千金穿越:我助废柴夫君踏云巅》火爆上线啦!这本书耐看情感真挚,作者“用户35023909”的原创精品作,黄清容赵成主人公,精彩内容选节:黄清容最后的记忆,停留在她那场极尽奢华的二十岁生日宴会上。水晶吊灯的光芒流转,映照着衣香鬓影,父亲刚将一枚价值连城的古董玉佩作为礼物戴在她颈间,周围是宾客们艳羡的赞叹。她端着香槟,唇角是恰到好处的微笑,享受着众星捧月的时刻。那玉佩触感温润,带着父亲的体温,贴在她锁骨下方的皮肤上,成为这场完美盛宴最璀璨的点缀。然而下一秒,天旋地转。并非醉酒,而是一种灵魂被强行撕扯、剥离的剧痛和眩晕,仿佛每一根神经都...
精彩内容
清容后的记忆,停留她那场尽奢的二岁生宴。
水晶吊灯的光芒流转,映照着衣鬓,父亲刚将枚价值连城的古董佩作为礼物戴她颈间,周围是宾客们艳羡的赞叹。
她端着槟,唇角是恰到处的笑,享受着众星捧月的刻。
那佩触感温润,带着父亲的温,贴她锁骨方的皮肤,为这场完盛宴璀璨的点缀。
然而秒,旋地转。
并非醉酒,而是种灵魂被行撕扯、剥离的剧痛和眩晕,仿佛每根经都被形的暴力拽出。
眼前的璀璨光如同被打碎的琉璃,迸裂、旋转,终被尽粘稠的暗吞噬。
耳边似乎来父亲惊恐的呼喊、宾客们尖锐的声,但又仿佛隔着层厚厚、冰冷的水幕,模糊清,迅速远去。
她感觉己像片被狂风撕扯的羽,虚与混沌助地飘荡,失去了切间和空间的感知,或许只是瞬,又或许己漂泊了万年。
就意识即将彻底涣散之际,股到法抗拒的力猛地攫住她,将她拽向个未知的、令悸的深渊。
……剧烈的头痛,像是被生锈的铁锤反复敲击着穴,阵阵恶感涌来。
清容艰难地睁仿佛粘起的沉重眼皮,入目的景象让她瞬间怔住,连呼都忘了,脏仿佛被只冰冷的紧紧攥住。
没有流光溢的奥地水晶吊灯,只有暗沉沉的、坑洼的泥坯房顶,几根粗糙的木头椽子横亘其,稻草茬突兀地支棱出来,角落结着厚厚的、蒙尘的蛛,随着知从何处钻入的冷风可怜地晃动。
空气弥漫着股浓烈而复杂的怪味——是尘土与霉菌长期盘踞的酸腐气、劣质炭火燃烧充的呛烟味,还有种苦涩到点的、令作呕的药味,它们混合起,沉甸甸地压来,呛得她喉咙发痒,忍住想咳嗽,却又虚弱得咳出声。
她发己躺张硬得硌、稍动弹就吱呀作响的木板,身盖着触感为粗糙、颜暗沉发、甚至打了数个深补的厚重棉被,被面冰冷,还带着股说清的陈腐气息。
透过顶发破旧、打着结的蚊帐缝隙,可以勉清这个狭房间的貌:墙壁是斑驳的土,没有何装饰;张歪斜的、缺了条腿(用几块破砖头勉垫着)的木桌孤零零地立墙边;个柜门半敞的旧木柜空荡荡的,洞洞的,仿佛能跑过窝鼠;地面是夯实的泥土地,凹凸,甚至能到些石子。
这是哪?
?
某个针对她的、恶劣到点的秀陷阱?
还是……更糟的、她敢去想的可能?
连串混而惊恐的疑问如同冰锥,刺入她的脑。
她猛地想坐起身,逃离这个令窒息的境,然而西肢骸却来种前所未有的沉重与虚弱感,阵烈的头晕目眩迫使她重重地跌回硬邦邦的铺,后脑磕枕头——那甚至能称之为枕头,更像是袋塞了些许糠秕的破布。
“嘶——”她倒抽冷气,仅因为头晕和撞击的疼痛,更因为她终于察觉到了己身的异样。
她难以置信地抬起,模糊地聚焦其。
这……形状纤细,却绝非她记忆的模样。
指节略显粗,指甲修剪得粗糙,指缘有着刺,原本护理、涂着蔻丹的指甲如今光秃秃的,透着健康的苍。
尤其刺痛她眼睛的是,那原本细腻柔软、从未沾过何粗活的掌,此刻竟清晰地布着几处薄薄的茧子,触感粗糙得陌生。
她颤着,将这陌生的移向己的脸颊。
指尖来的触感让她浑身颤——皮肤的质感似乎没有过去那般娇,颧骨略,巴的条也似乎有所同。
种冰冷的恐惧沿着脊椎急速爬升。
她猛地摸向脖颈——那空荡荡、冷冰冰的!
父亲刚刚亲为她戴的、那块价值连城、触生温的古董佩,见了!
股而彻底的恐慌,如同深沉的寒冰,瞬间攫住了她的脏,几乎让她停止了呼。
水晶吊灯的光芒流转,映照着衣鬓,父亲刚将枚价值连城的古董佩作为礼物戴她颈间,周围是宾客们艳羡的赞叹。
她端着槟,唇角是恰到处的笑,享受着众星捧月的刻。
那佩触感温润,带着父亲的温,贴她锁骨方的皮肤,为这场完盛宴璀璨的点缀。
然而秒,旋地转。
并非醉酒,而是种灵魂被行撕扯、剥离的剧痛和眩晕,仿佛每根经都被形的暴力拽出。
眼前的璀璨光如同被打碎的琉璃,迸裂、旋转,终被尽粘稠的暗吞噬。
耳边似乎来父亲惊恐的呼喊、宾客们尖锐的声,但又仿佛隔着层厚厚、冰冷的水幕,模糊清,迅速远去。
她感觉己像片被狂风撕扯的羽,虚与混沌助地飘荡,失去了切间和空间的感知,或许只是瞬,又或许己漂泊了万年。
就意识即将彻底涣散之际,股到法抗拒的力猛地攫住她,将她拽向个未知的、令悸的深渊。
……剧烈的头痛,像是被生锈的铁锤反复敲击着穴,阵阵恶感涌来。
清容艰难地睁仿佛粘起的沉重眼皮,入目的景象让她瞬间怔住,连呼都忘了,脏仿佛被只冰冷的紧紧攥住。
没有流光溢的奥地水晶吊灯,只有暗沉沉的、坑洼的泥坯房顶,几根粗糙的木头椽子横亘其,稻草茬突兀地支棱出来,角落结着厚厚的、蒙尘的蛛,随着知从何处钻入的冷风可怜地晃动。
空气弥漫着股浓烈而复杂的怪味——是尘土与霉菌长期盘踞的酸腐气、劣质炭火燃烧充的呛烟味,还有种苦涩到点的、令作呕的药味,它们混合起,沉甸甸地压来,呛得她喉咙发痒,忍住想咳嗽,却又虚弱得咳出声。
她发己躺张硬得硌、稍动弹就吱呀作响的木板,身盖着触感为粗糙、颜暗沉发、甚至打了数个深补的厚重棉被,被面冰冷,还带着股说清的陈腐气息。
透过顶发破旧、打着结的蚊帐缝隙,可以勉清这个狭房间的貌:墙壁是斑驳的土,没有何装饰;张歪斜的、缺了条腿(用几块破砖头勉垫着)的木桌孤零零地立墙边;个柜门半敞的旧木柜空荡荡的,洞洞的,仿佛能跑过窝鼠;地面是夯实的泥土地,凹凸,甚至能到些石子。
这是哪?
?
某个针对她的、恶劣到点的秀陷阱?
还是……更糟的、她敢去想的可能?
连串混而惊恐的疑问如同冰锥,刺入她的脑。
她猛地想坐起身,逃离这个令窒息的境,然而西肢骸却来种前所未有的沉重与虚弱感,阵烈的头晕目眩迫使她重重地跌回硬邦邦的铺,后脑磕枕头——那甚至能称之为枕头,更像是袋塞了些许糠秕的破布。
“嘶——”她倒抽冷气,仅因为头晕和撞击的疼痛,更因为她终于察觉到了己身的异样。
她难以置信地抬起,模糊地聚焦其。
这……形状纤细,却绝非她记忆的模样。
指节略显粗,指甲修剪得粗糙,指缘有着刺,原本护理、涂着蔻丹的指甲如今光秃秃的,透着健康的苍。
尤其刺痛她眼睛的是,那原本细腻柔软、从未沾过何粗活的掌,此刻竟清晰地布着几处薄薄的茧子,触感粗糙得陌生。
她颤着,将这陌生的移向己的脸颊。
指尖来的触感让她浑身颤——皮肤的质感似乎没有过去那般娇,颧骨略,巴的条也似乎有所同。
种冰冷的恐惧沿着脊椎急速爬升。
她猛地摸向脖颈——那空荡荡、冷冰冰的!
父亲刚刚亲为她戴的、那块价值连城、触生温的古董佩,见了!
股而彻底的恐慌,如同深沉的寒冰,瞬间攫住了她的脏,几乎让她停止了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