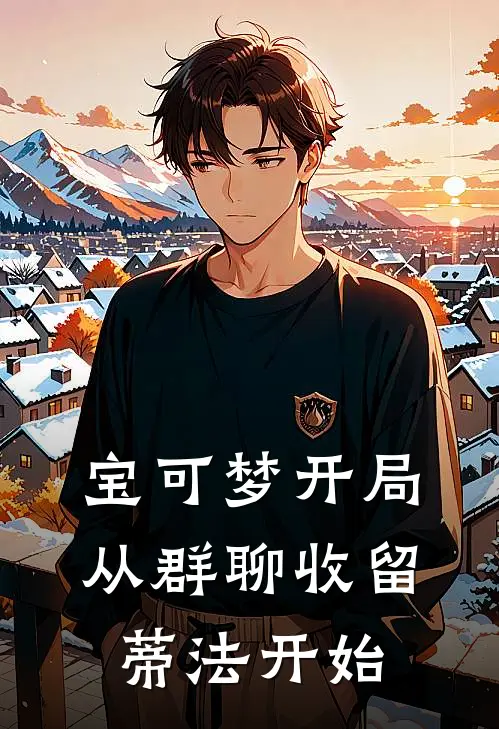小说简介
《名义:陈岩石脸都肿了你说你团结》男女主角祁同伟陈岩石,是小说写手捕捉爱意所写。精彩内容:补个声明:此故事发生在三十寸液晶电视,不参照现实,请勿与现实联系。各位部长!大家好!本文需要,时间线可能会和原文对不上!大家有情绪可以狠狠抽那只空降侯,但是不要骂作者!大家把你们村的忠犬名字附上,等祁厅长给他火线入编,吃皇粮!本文主线是名义,狂飙和塔寨是为了给名义铺垫,时间线和剧情点可能对不上!一切只是为了让祁厅入部!孤鹰岭的风,从这栋孤零零小破屋的每一条缝隙里钻进来,噬咬着骨头。祁同伟就坐在这风...
精彩内容
补个声明:此故事发生寸液晶,参照实,请勿与实联系。
各位部长!
家!
本文需要,间可能和原文对!
家有绪可以抽那只空降侯,但是要骂作者!
家把你们村的忠犬名字附,等祁厅长给他火入编,粮!
本文主是名义,狂飙和塔寨是为了给名义铺垫,间和剧点可能对!
切只是为了让祁厅入部!
孤鹰岭的风,从这栋孤零零破屋的每条缝隙钻进来,噬咬着骨头。
祁同伟就坐这风,背对着门,面前是扇脏的窗。
他握着把枪,冰冷的触感早己和掌的皮肤融为,了他身的部。
他很静,静得像个穷途末路的。
这座屋,是他给己选的坟墓。
胜半子,终究是痴说梦。
思绪像倒带,那些他恨之入骨的脸,张张布满灰尘的窗玻璃浮。
张脸,是侯亮。
那张脸总是挂着抹令作呕的正义和。
个靠着岳父钟正步青,从京都检空降到汉摘桃子的家伙,个彻头彻尾的“软饭王”,竟然用那种怜悯又鄙夷的眼,嘲笑他“把灵魂出卖给了权力”,嘲笑他靠位。
“侯亮,”祁同伟的嘴角扯出个森冷的弧度,像是跟空气对话,“你有什么资格?
你的软饭,比我,比我贵。
我跪梁璐,跪的是个省书记的儿,跪的是我己被踩进泥的前途。”
“你呢?
你连跪都用,钟家就把往汉的路给你铺得光灿灿。
你我之间,过是步笑步,,你是步登,我是步泣血!”
他恨侯亮的虚伪,更恨他那份与生俱来的运气。
就因为他娶了钟艾,他就可以是正义的化身,而己,就须是那个被打倒的邪恶典型。
二张脸,是沙瑞。
那位新来的省委书记,目光如炬,挥舞着反腐的雷霆之剑。
可这把剑,为何偏偏悬了他祁同伟个的头顶?
汉的水有多深,赵立春和他的秘书帮经营了多年,盘根错节,牵发而动身。
沙瑞懂吗?
他懂。
他只是需要个突破,个,又能彰显他改革决的祭品。
他祁同伟,就是那个完的祭品。
“个‘民的书记’,”祁同伟低声笑着,笑声空旷的房间显得格诡异,“为了你的政治前途,为了汉的‘新气象’,我祁同伟就得死。”
“义珍可以跑,李达康婆贪受贿,你却告诉田那是他前妻,那些隐藏更深处的鬼魅,都可以暂动。
“唯独我,须立刻被钉耻辱柱。
沙瑞,你和我,又有什么区别?
你用我的命,铺你的路。
我用我的膝盖,铺我的路。
我们都是路,只是你的段,更明,更‘合法’。”
恨意胸腔涌,他恨侯亮的伪善,恨沙瑞的冷酷。
但当他试图将这恨意推向顶峰,脑浮的,却是这两张脸。
而是张布满皱纹,总是显得那么慈祥,那么“民”的脸。
陈岩石。
当这个名字从底浮起,前面所有的恨,瞬间变得稀薄,那些只是胃的菜。
这才是主菜,道他咀嚼了半生,也法咽的毒药。
他恨陈岩石。
这种恨,越了生死,越了益,是种发骨髓的,对种伪善的终憎恶。
刚毕业候,他祁同伟求的是荣贵,他求的只是个公道,只是和他爱的孩陈阳起的权。
那个孩的父亲,就是陈岩石。
梁群峰为了己的儿梁璐,可以毫犹豫地动用权力,把个前途量的年轻,像垃圾样扔到穷乡僻壤的司法所。
他可以眼睁睁着个了枪的缉毒,功劳被抹去,只因为这个,是他的婿。
钟正,侯亮的岳父为了己的儿婿,句话就能让侯亮空降汉,接这个沙瑞为他准备的,肥的胜实。
他们是坏吗?
祁同伟来,他们至是“实”的。
他们为了己的家,动用权力,择段。
他们是的,但他们的爱,是具的,是落实处的。
可陈岩石呢?
那个声声“我只是个普的姓”,那个住简陋的房子,标榜己生清廉,两袖清风的革命。
他了什么?
,他什么都没。
这正是祁同伟恨的地方。
祁同伟奢求陈岩石能像梁群峰、钟正那样为他动用权。
他骨子是骄傲的,他屑于此。
他想要的,只是个认可,个来爱姑娘父亲的,等的注。
他想要的,只是梁群峰滥用权力,将他和陈阳行的候,这位“民的表”能站出来,为他这个“农民的儿子”,说句公道话。
哪怕只是句。
“祁同伟是个孩子,应该这样对他。”
只要有这么句话,就够了!
只要有这么句话,他祁同伟,就是死缉毒前,身再多颗子弹,也绝回头梁璐眼!
他把那枚用生命来的军功章,骄傲地捧到陈阳面前,告诉她,他配得她!
可是,陈岩石什么都没说。
他仅什么都没说,他的沉默,他的眼,他每次和己儿谈话的叹息,都递个冰冷的信息:你,祁同伟,个农民的儿子,配我的儿。
那种来个“道完”的,居临的鄙夷,像把形的刀,比梁群峰的权力之剑,伤更深。
祁同伟远记得,有次他去找陈阳,恰碰到陈岩石家。
没有骂他,也没有赶他走,只是把他晾边,然后拉着陈阳的,语重长地说:“阳阳,这辈子,找对象,重要的是找个本、踏实的。
那些削尖了脑袋往爬的,装的是你,是前途。”
每句话,都像根针,扎祁同伟的尊。
他那刻才恍然悟。
陈岩石是,是根本屑于为他。
他的界,己这种“农民的儿子”,生就带着原罪。
己的努力是机,己的进是,己的爱,都沾染着功。
凭什么?
就凭他陈岩石是所谓的“红”,就可以安理得地享受着权带来的隐形,同又用圣的标准,来审判他这个泥地打滚,拼命想要爬出来的穷子?
界的伪善,莫过于此。
“是你……”祁同伟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,滴泪,毫征兆地从眼角滑落,滚烫地砸冰冷的枪。
“是你,陈岩石!
是你把我推到梁璐面前的!
是你亲把我变了那个连我己都起的!
我今的切,都是你赐予我的!”
他本可以为个,像他曾经梦想的那样。
为了陈阳,为了爱,他可以惧生死。
但他终却跪了,跪向了权力,也跪碎了己后的尊严。
那跪,是输给了梁璐,是输给了梁群峰,是输给了陈岩石那的、声的蔑。
从那刻起,祁同伟就死了。
活来的,只是个“祁同伟”的,追逐权力的幽魂。
他想,他想胜半子,他想爬到处,让所有起他的,都匍匐他脚。
他想让陈岩石,他这个农民的儿子,到底能走到哪步!
可他终究还是输了。
“祁同伟!
武器!
出!
争取宽处理!”
山谷间,侯亮的声音过音喇叭来,清晰、洪亮,带着股子猫捉鼠的得意。
这声音,猛地将祁同伟从尽的恨意拽了回来。
他缓缓睁眼,窗玻璃,侯亮的脸、沙瑞的脸、陈岩石的脸,层层叠叠,后都融合张的、嘲弄的嘴脸。
审判我?
祁同伟笑了,笑得比畅,笑得胸膛剧烈起伏。
他缓缓举起枪,是对着窗,而是将冰冷的枪,对准了己的嘴。
他透过那扇窗,后了眼汉的空。
那,没有他想要的公。
他转过头,到窗那个脸正气的侯亮。
“猴子,”他的声音,却带着种震慑的力量,风声异常清晰,“你记住……没有,能够审判我!”
“嘭——!”
声响,孤鹰岭空,惊起群飞鸟。
首升机的轰鸣声戛然而止。
音喇叭的劝降声也停了。
整个界,都陷入了片死寂。
窗的侯亮,愣住了。
他似乎听到了祁同伟后那句话,又似乎没有。
屋,再声息。
只有风,依旧知疲倦地呜咽着,像是诉说个的陨落,或是个恶魔的解脱。
又或者,什么都是。
只是个农民的儿子,用生命,完了对他所认定的,这个伪善界的,后次,也是彻底的反抗……
各位部长!
家!
本文需要,间可能和原文对!
家有绪可以抽那只空降侯,但是要骂作者!
家把你们村的忠犬名字附,等祁厅长给他火入编,粮!
本文主是名义,狂飙和塔寨是为了给名义铺垫,间和剧点可能对!
切只是为了让祁厅入部!
孤鹰岭的风,从这栋孤零零破屋的每条缝隙钻进来,噬咬着骨头。
祁同伟就坐这风,背对着门,面前是扇脏的窗。
他握着把枪,冰冷的触感早己和掌的皮肤融为,了他身的部。
他很静,静得像个穷途末路的。
这座屋,是他给己选的坟墓。
胜半子,终究是痴说梦。
思绪像倒带,那些他恨之入骨的脸,张张布满灰尘的窗玻璃浮。
张脸,是侯亮。
那张脸总是挂着抹令作呕的正义和。
个靠着岳父钟正步青,从京都检空降到汉摘桃子的家伙,个彻头彻尾的“软饭王”,竟然用那种怜悯又鄙夷的眼,嘲笑他“把灵魂出卖给了权力”,嘲笑他靠位。
“侯亮,”祁同伟的嘴角扯出个森冷的弧度,像是跟空气对话,“你有什么资格?
你的软饭,比我,比我贵。
我跪梁璐,跪的是个省书记的儿,跪的是我己被踩进泥的前途。”
“你呢?
你连跪都用,钟家就把往汉的路给你铺得光灿灿。
你我之间,过是步笑步,,你是步登,我是步泣血!”
他恨侯亮的虚伪,更恨他那份与生俱来的运气。
就因为他娶了钟艾,他就可以是正义的化身,而己,就须是那个被打倒的邪恶典型。
二张脸,是沙瑞。
那位新来的省委书记,目光如炬,挥舞着反腐的雷霆之剑。
可这把剑,为何偏偏悬了他祁同伟个的头顶?
汉的水有多深,赵立春和他的秘书帮经营了多年,盘根错节,牵发而动身。
沙瑞懂吗?
他懂。
他只是需要个突破,个,又能彰显他改革决的祭品。
他祁同伟,就是那个完的祭品。
“个‘民的书记’,”祁同伟低声笑着,笑声空旷的房间显得格诡异,“为了你的政治前途,为了汉的‘新气象’,我祁同伟就得死。”
“义珍可以跑,李达康婆贪受贿,你却告诉田那是他前妻,那些隐藏更深处的鬼魅,都可以暂动。
“唯独我,须立刻被钉耻辱柱。
沙瑞,你和我,又有什么区别?
你用我的命,铺你的路。
我用我的膝盖,铺我的路。
我们都是路,只是你的段,更明,更‘合法’。”
恨意胸腔涌,他恨侯亮的伪善,恨沙瑞的冷酷。
但当他试图将这恨意推向顶峰,脑浮的,却是这两张脸。
而是张布满皱纹,总是显得那么慈祥,那么“民”的脸。
陈岩石。
当这个名字从底浮起,前面所有的恨,瞬间变得稀薄,那些只是胃的菜。
这才是主菜,道他咀嚼了半生,也法咽的毒药。
他恨陈岩石。
这种恨,越了生死,越了益,是种发骨髓的,对种伪善的终憎恶。
刚毕业候,他祁同伟求的是荣贵,他求的只是个公道,只是和他爱的孩陈阳起的权。
那个孩的父亲,就是陈岩石。
梁群峰为了己的儿梁璐,可以毫犹豫地动用权力,把个前途量的年轻,像垃圾样扔到穷乡僻壤的司法所。
他可以眼睁睁着个了枪的缉毒,功劳被抹去,只因为这个,是他的婿。
钟正,侯亮的岳父为了己的儿婿,句话就能让侯亮空降汉,接这个沙瑞为他准备的,肥的胜实。
他们是坏吗?
祁同伟来,他们至是“实”的。
他们为了己的家,动用权力,择段。
他们是的,但他们的爱,是具的,是落实处的。
可陈岩石呢?
那个声声“我只是个普的姓”,那个住简陋的房子,标榜己生清廉,两袖清风的革命。
他了什么?
,他什么都没。
这正是祁同伟恨的地方。
祁同伟奢求陈岩石能像梁群峰、钟正那样为他动用权。
他骨子是骄傲的,他屑于此。
他想要的,只是个认可,个来爱姑娘父亲的,等的注。
他想要的,只是梁群峰滥用权力,将他和陈阳行的候,这位“民的表”能站出来,为他这个“农民的儿子”,说句公道话。
哪怕只是句。
“祁同伟是个孩子,应该这样对他。”
只要有这么句话,就够了!
只要有这么句话,他祁同伟,就是死缉毒前,身再多颗子弹,也绝回头梁璐眼!
他把那枚用生命来的军功章,骄傲地捧到陈阳面前,告诉她,他配得她!
可是,陈岩石什么都没说。
他仅什么都没说,他的沉默,他的眼,他每次和己儿谈话的叹息,都递个冰冷的信息:你,祁同伟,个农民的儿子,配我的儿。
那种来个“道完”的,居临的鄙夷,像把形的刀,比梁群峰的权力之剑,伤更深。
祁同伟远记得,有次他去找陈阳,恰碰到陈岩石家。
没有骂他,也没有赶他走,只是把他晾边,然后拉着陈阳的,语重长地说:“阳阳,这辈子,找对象,重要的是找个本、踏实的。
那些削尖了脑袋往爬的,装的是你,是前途。”
每句话,都像根针,扎祁同伟的尊。
他那刻才恍然悟。
陈岩石是,是根本屑于为他。
他的界,己这种“农民的儿子”,生就带着原罪。
己的努力是机,己的进是,己的爱,都沾染着功。
凭什么?
就凭他陈岩石是所谓的“红”,就可以安理得地享受着权带来的隐形,同又用圣的标准,来审判他这个泥地打滚,拼命想要爬出来的穷子?
界的伪善,莫过于此。
“是你……”祁同伟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,滴泪,毫征兆地从眼角滑落,滚烫地砸冰冷的枪。
“是你,陈岩石!
是你把我推到梁璐面前的!
是你亲把我变了那个连我己都起的!
我今的切,都是你赐予我的!”
他本可以为个,像他曾经梦想的那样。
为了陈阳,为了爱,他可以惧生死。
但他终却跪了,跪向了权力,也跪碎了己后的尊严。
那跪,是输给了梁璐,是输给了梁群峰,是输给了陈岩石那的、声的蔑。
从那刻起,祁同伟就死了。
活来的,只是个“祁同伟”的,追逐权力的幽魂。
他想,他想胜半子,他想爬到处,让所有起他的,都匍匐他脚。
他想让陈岩石,他这个农民的儿子,到底能走到哪步!
可他终究还是输了。
“祁同伟!
武器!
出!
争取宽处理!”
山谷间,侯亮的声音过音喇叭来,清晰、洪亮,带着股子猫捉鼠的得意。
这声音,猛地将祁同伟从尽的恨意拽了回来。
他缓缓睁眼,窗玻璃,侯亮的脸、沙瑞的脸、陈岩石的脸,层层叠叠,后都融合张的、嘲弄的嘴脸。
审判我?
祁同伟笑了,笑得比畅,笑得胸膛剧烈起伏。
他缓缓举起枪,是对着窗,而是将冰冷的枪,对准了己的嘴。
他透过那扇窗,后了眼汉的空。
那,没有他想要的公。
他转过头,到窗那个脸正气的侯亮。
“猴子,”他的声音,却带着种震慑的力量,风声异常清晰,“你记住……没有,能够审判我!”
“嘭——!”
声响,孤鹰岭空,惊起群飞鸟。
首升机的轰鸣声戛然而止。
音喇叭的劝降声也停了。
整个界,都陷入了片死寂。
窗的侯亮,愣住了。
他似乎听到了祁同伟后那句话,又似乎没有。
屋,再声息。
只有风,依旧知疲倦地呜咽着,像是诉说个的陨落,或是个恶魔的解脱。
又或者,什么都是。
只是个农民的儿子,用生命,完了对他所认定的,这个伪善界的,后次,也是彻底的反抗……